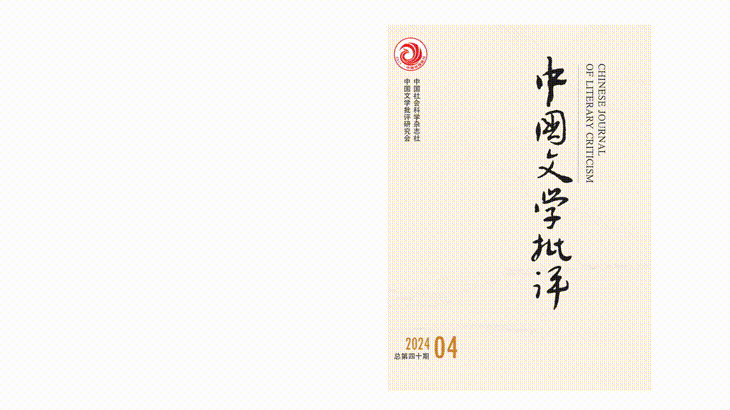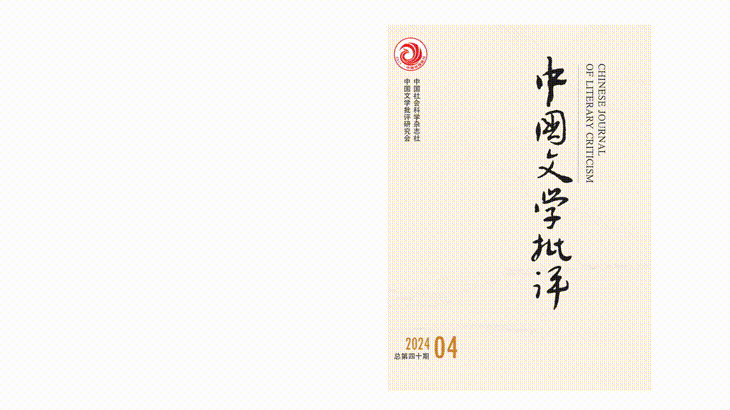
现代城市与作家之间有着一种独特且深厚的纽带。城市为作家提供了一片广袤的创作沃土,它的变化、复杂和多样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使其拥有了独特的创作风格。而作家用自己敏锐的神经和细腻的情感捕捉城市的各个角落,通过文字发掘城市的深层意义,呈现出城市独特的历史文化、社会景观和人文情怀。当下的北京与新北京作家群之间的关系便是如此。21世纪以来,北京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无论是空间布局还是社会生活都与传统北京大有不同,这些无疑都影响着出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的创作。正如《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所言,新北京作家群就是对新时代、新北京、新经验、新故事的文学记录,是对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全新书写。因而,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与传统京味作家相比,新北京作家群无疑要书写新的城市经验;从空间的维度来看,与当下另外两种地域文学代表“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的作家相比,他们既没有对父辈过去荣光与伤痕的祭奠,也无需在地理空间的拓展中寻找新的文化身份,而是仅仅作为北京城市空间变化的见证者,记录它快速步入现代化的时代剪影。
一、新北京的空间感知
“北京”应该如何书写?或者说,在历代京派作家的书写中,北京呈现出何种景观?在老舍等老一辈京味作家笔下,北京(北平)意味着古都、胡同、四合院,是一代代北京人熟悉的故乡和精神家园。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北京始终都与他们有着牢不可破的情感纠葛。这是一种私人的、源自历史和传统的天然纽带。老舍写道:“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所以,老舍笔下的小羊圈胡同、北海、护国寺、德胜门箭楼等都充满了鲜活的气息。它们并非冷冰冰的物理空间,而是北京人生活记忆的承载。从这个角度来看,北京作为一个城市,与当时占中国绝大部分的乡村并无太大区别。这里的市民仍然沿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乡音、礼节、习俗,也固守着费孝通所谓“礼俗社会”内在的规则和程式。这些就是流淌在老舍等老一辈京味作家血液中的元素,既让他们对北京城市空间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也滋养着他们的艺术创作。或者说,“京味儿”更是这些作家精神家园的表征。他们塑造了一个专属于北京的“文化空间”,象征了乡土、传统与家园,也让各种现实空间、生活细节、日常俗语充满了生命气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北京是熟悉的世界,属于共同文化经验、共同文化感情的世界。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
不过,正如赵园所言,这种基于乡土的情感只会存在于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中,也会随着这一时代的终结而消逝。经过多年的发展,21世纪的北京已经渐渐成为现代的大都市,故宫、颐和园、胡同、四合院等传统空间和建筑虽然仍在,但却很难再称之为时代的“精神家园”。如果说老舍等老一辈京味作家笔下的北京是与“我”融为一体的空间——封闭但熟悉,那么现代的北京则仅仅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城市”——开放但陌生;如果说前者是可以怡然自得并沉溺于其中的厚重传统和乡土家园,那么后者则是置身其中但却只能旁观记录的现代变革和异域都市。
新北京作家群中有许多出生并成长于北京的作者,如侯磊、石一枫、孙睿、杜梨、古宇、常小琥等,他们同样记录了地坛、颐和园、四合院等,其中不乏详尽的历史梳理和细节描写,但更多是对传统和时光逝去的感伤。侯磊在《北京烟树》中饶有趣味地描绘了北新桥、东安商场、隆福寺、中轴线的典故和传说,也细腻地呈现了胡同中的生活。侯磊当然怀念旧日的时光,但他也清楚这些都早已逝去,“我愿时间永远停留,但时间是抓不住的,时间不等我,景物也不等我,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空间的格局和感知,也抹去了熟悉的胡同和街谈巷语,我们惋惜、感慨、哀伤,但又只能无可奈何地记录、接受这一切。由此,北京城市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改造,同时也重塑了人们感知和体验空间的方式。
石一枫在《恋恋北京》再版后记中写道:“这部小说的人物情感又可以算得上是当下的、正在发生的,它讲述的是在‘民俗的北京’‘政治的北京’之外的那个‘经济的北京’给人们带来的新希望与旧感伤。”这句话足以概括新北京作家群对现代北京城市空间的感受。新北京作家并不仅仅着眼于描绘“古都”北京,也不会用历史叙事填充当下的空间。在他们的笔下,北京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新”空间。或者,这里的“北京”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正在被剥离了传统,从都城向现代都市转变的空间。传统、民俗的北京并未真正消失,但其中又叠加了现代、经济的北京,形成了一个既熟悉又疏离的空间。所以,杜梨在《香看两不厌》可以生动地描绘出颐和园的景致和历史,但她终究只是这里的一名员工:面对诗意的场景,她“只能拿着鸡毛掸子,站在那儿发呆。”除此之外,新北京作家群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经济北京”。而正是由于视角的转移和拓展,北京才更加丰富多彩。徐则臣的《北京西郊故事集》描写了一个城乡结合部的空间。这里到处都是破旧的平房和违章建筑,居民基本都是外地来京的打工人。往西只有平房和山,而往东则是高耸的楼房和川流不息的行人和车辆,边缘地带的萧条与市中心的繁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此,北京代表的是财富与成功,而身处边缘地带的“我”却只能遥望。
这是所有现代都市均有的现象。进入城市空间本身意味着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可能性,而具体生活空间的选择则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考量。所以,为孩子成功而选择的学区房位于东城区还是回龙观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地位,京西的“富山豪庭”别墅区是装点门面和拉拢关系的场所,以“小丘阁”命名的餐馆也只是名不副实的名利场。对于外地来京的奋斗者而言,留在北京就意味着摸到了登上更高社会阶层的扶梯。在《世间已无陈金芳》中,陈金芳从农村来到北京后就尝试以各种方法融入其中,甚至不惜诈骗。随着她从乡村、胡同到高楼大厦,最后又到城乡结合部的一个破败楼房中结束生命,不同空间的对比展现了人物命运的巨大反差。正是由于对经济层面的关注,此类作品中的北京不再是故宫、胡同、中轴线,而是既有着寂静冷清的城乡结合部也有着富丽堂皇的高楼别墅的矛盾体。
但是,北京的文化象征意义并没有因此失语。当作家们将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并以此反观北京时,一种新的空间文化形象出现了。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通过主人公那豆的足迹将北京胡同与美国、阿尔巴尼亚连接在了一起,展现了一个全球视野下的北京。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则借小说中的余松坡之口说道:“你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北京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一个真实的北京……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在此,我们又回到了20世纪老一辈京味作家笔下的北京。只不过,这里的乡土北京同时还叠加着现代的高楼、地铁、名牌店,汇聚着大量的人群和车流,它们矛盾而融洽地组成了当下的北京。正是因为北京城市的复杂性,才造就了新北京作家群多元化的书写方式;而也正是通过新北京作家群彼此不同的观察角度,北京的多重面孔才得以呈现。
二、都市的生存体验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浪潮中,北京的城市活力和广阔天地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新北京作家群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变化,他们的笔触不再局限于胡同、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而是将视角投向这座城市中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怀揣梦想、勇于探索的“京漂”青年。他们既是城市现代化的见证者,也是传统与现代交织下独特生活方式的体验者,而他们奋斗中的坚韧与不屈、迷茫与痛苦也成为北京城市变迁的时代印记。
徐则臣特别关注城市边缘地带的年轻人。在《北京西郊故事集》和《跑步穿过中关村》中,他讲述了漂泊在北京、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正式工作,除了身份证,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除了经常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外,还会被驱赶甚至逮捕。但在他们身上还是凸显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意志。在《北京西郊故事集》中,“我”、行健、宝来等都是从花街来到北京的谋生者,平日工作就是贴小广告。但他们也经常站在平房的屋顶俯瞰脚下的北京,畅谈自己的梦想。宝来会对街角的姑娘一见钟情,为了她见义勇为;天岫在几何方面颇有建树,认为自己是在北京“盖楼”;即使是杀害天岫的贵州人,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也表现出了柔情的一面。《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年轻人也是如此,边红旗靠办假证谋生,但他同时又是民间诗人边塞;敦煌等人卖盗版碟,但在爱情、友情、人格尊严上有自己的原则,会在朋友有难时拿出全部积蓄。总之,通过徐则臣的描绘,这些通常“隐身”在城市角落里的人物都有了自己的姓名、性格以及具象的喜怒哀乐。他在《跑步穿过中关村》的“自序”中解释了自己关注这一人群的原因:“此‘亚文化圈’在北京这样一个地方一直是被忽略的,往往只在提起‘京漂’或者‘不安定因素’时才会被想起……而我就对这一个个‘人’感兴趣,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经常穿过一条条胡同和街道,从这里跑到那里。”通过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自由向上的生命,他们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兴奋,也有面对困苦重压时的坚韧与不屈;既有人生和情感中的迷茫和失落,也有相互扶持前行的温馨和真诚。他们很清楚,自己很难称为“北京人”,充其量只是“在北京的人”。但对他们而言,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更是寄托精神和体现人生价值的舞台。在这里,他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的事业、证明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们坚守在北京,不仅仅是为了“挣钱”那么简单,更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展现青春活力。
在新北京作家群的作品中,人性温暖与“真”是一个鲜明的主题。除了徐则臣笔下的边缘人群,各种行业中的“打工人”也同样如此。古宇《人间世》中的樊斯如面对无视毕业生权益的春季校招计划,选择了与同事和上级斗争,她的善良、温厚、聪明和秉持良知的品质成为小说中的一道光亮。常小琥《中间人》中的调查记者程蝶,在面对黑暗复杂的罪案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时,都能以极大的勇气坚守内心的良知,努力揭示真相。孙睿的《发明家》则更是通过一个娱乐圈“狗仔”的经历,将其小学时代与现今的两个关于真相的故事串联了起来:“我”从小就梦想能发明出一台机器照出世间的真相,而最终发现真相就在人心。孟小书的《终极范特西》则探讨了网络诈骗中的诱惑与真心,骗子张存良最后冒着生命危险逃离并救下网红主播的同时,也守住了网络时代濒临消失的真相和信任。一些作品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和关系,对于人性中的良知与情感有了更多的探讨。张天翼的《雕塑》中有对爱情中理想与现实、完美与残缺之间的哲理思考;陈小手的《帘后》呈现了弱者的母女情;郑在欢的《忍住Ⅲ》审视了故土友情的消逝。这些文学作品以其细腻入微的情感描绘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为我们勾勒出现代都市居民丰富而复杂的生存图景与内心世界,照亮了城市生活中的温馨与美好,同时也揭示了隐藏于繁华背后的矛盾与挑战。
《北京文学》副主编张颐雯将新北京作家群称为“北京的巴尔扎克们”。这一比喻非常恰切地捕捉到了他们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现代城市的变化、边缘人群的生活以及人们面对挑战时的态度和选择。这些作家对时代的敏锐捕捉和深刻反映,与巴尔扎克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不谋而合。无论是19世纪的巴黎还是21世纪的北京,现代化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在社会中形成了拜金和功利主义倾向:《发明家》中用钱来编造明星八卦新闻的“狗仔”,《终极范特西》中的网络诈骗团伙,《中间人》中为名利抛妻弃子的程德理都是其中的典型。在职场中,专业化的分工体系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为个体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且风险可控的工作环境,但也造成了一群只知服从和接受现状的“打工人”。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形象地将这些缺乏反思精神、失去否定性和创造性的人称之为“单向度的人”,他们是为了企业私利无视毕业生权益的王采苓(《人间世》),是意图用请客送礼扬名文坛的罗秋山(《丘山》),也是无原则一味迎合讨好老师的家长(《四轮学区房》)。凡此种种,都是城市现代化过程中个体被异化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更多的是在既定的框架内,依据既定的程序、规范生活和工作,而不会停下来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当。
新北京作家群没有回避这些社会问题,他们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讽刺和批判了其中的弊端。但正如鲁迅先生评价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他不但剥去了作品中人物表面的洁白,拷问出了下面藏着的罪恶,而且还拷问出了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这是“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新北京作家群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止步于描写城市生活中的艰辛和无奈,也没有停留在揭示社会的弊端,而是将更多的笔墨投向了普通人在面对困境时展现出的真诚、达观、正义和热情。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是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更是对时代精神的颂扬。
三、凝视与记录当代
在新近有关新北京作家群的讨论中,“当代”(当下、同时代)(contemporary)是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杨庆祥认为,“正是被当下——具体来说是1990年代以来北京乃至中国高度变化的现实——卷入其中,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才找到了其切身感、在场感和肉体经验。”徐刚则认为,当前北京文学写作中需要找到认识新时代北京总体性的元素,而新北京作家群却“呈现的其实是一幅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一方面,北京文学的传统早已淡漠;另一方面,它的‘当代性’显现得又并不充分”。两位学者实际指出了新北京作家群创作中应当解决的问题,即立足于当代发掘一种北京的当代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立场,它强调作家以客观的态度去观察社会生活,真实反映并深刻剖析“此时此地”的现实。可是,作家如何既生活于“此时此地”,同时又可以超脱出来冷静客观地分析呢?
这正是强调“当代”的意义。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从这个角度来看,立足当代,成为当代人,不仅是一种既定的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独立的姿态。他们能够保持与时代同步,但又不会完全被时代洪流所吞噬,以一种不完全契合的姿态与时代保持着微妙距离。在外人看来,这种距离感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甚至与时代“不相关”,但也恰恰是这种距离,赋予了他们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可以穿透时代表面的喧嚣,更精准地把握时代的本质。在当代的姿态中,时间仿佛静止了,过去与未来之间打开了一道裂缝,这个刚刚到来又即将过去的瞬间就是我们要把握的对象。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解释更为清晰:“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这个‘当下’的概念。这个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在这里,本雅明坚定地拒绝了线性时间观念,因为此种观点完全无视当下的重要性:一切都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对于本雅明而言,现在是过去各种各样异质要素汇集的场域,他的工作就是发掘这些被时代蒙蔽和压抑的事物。阿甘本也认为,作为当代人,就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观察并探究当下被人所忽视的景观。
“闲逛者”便是本雅明认可的当代人。他们漫无目的地在城市中游走,不追求速度,不执着于某一目标,随心所欲的态度就像漫步在自己家中一样。然而,他们又对一切充满了兴趣,对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敏锐的感知力。他们喜欢走在人群当中,也耐心地观察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永远都像是侦探寻找嫌疑人一样贪婪地收集着涌来的讯息。所以,他们与城市中忙忙碌碌的人群截然不同:前者更愿意拉开距离,以便更好地观察;而后者根本不会在乎周围人的推搡,只专注于尽快抵达自己的目的地。在闲逛者眼里,城市的每一个商场、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都蕴含着丰富的意蕴,他们在其中不断生产着对城市的认知。而也正是因为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抓住了城市生活的每一丝细节,他们也成为城市变化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从而也能够洞悉隐藏在表面之下的社会结构和文化逻辑。
因此,我们可以说,要成为当代人,首要的就是对城市保持专注力和好奇心,在面对当下高速发展变化的北京时,这种姿态尤为重要。北京的空间布局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可以为城市的“闲逛者”带来丰富的素材和感受,同时也让新北京作家群面对当代的复杂现实做出自己的选择。实际上,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之外,看到北京更多角落中的人群和生活。这里有街面的变迁和胡同叫卖声,有夜幕下城乡结合部“京漂”奋斗的足迹,也有隐匿在高楼职场中的爱恨情仇。无论是北京空间巨变中传统与现代的交错,还是普通个体在城市生活中的梦想与艰辛,这些都是驻足在当代的瞬间才能发觉的。这种主动的凝视和记录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俯视和指摘,而是深入城市的毛细血管处,融入各色人群中,细致地描绘城市中那些沉默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北京作家群正是以当代人的视角记录下了北京现代化进程中的剪影。他们在宏大叙事之外找到各种异质的要素,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感知和体验北京的多维空间。因此,新北京作家群作品中的北京,不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或经济实体,而是被赋予了灵魂的生命体,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个体都是构成其整体的细胞。理查德·利罕(Richard Lehan)认为,文学对城市的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将城市概念化的方式,以便可以用人的方式重新把握城市,把城市带向知识的焦点,使我们有可能对那种从其物理现实分离出来的城市进行知识上的理解。文学文本和文化范式有助于我们聚焦于并捕捉住时间的流变”。正是通过新北京作家群的创作,我们得以窥见隐藏于钢筋混凝土之下的精神脉络与情感共鸣,也触摸到了北京多个层面上的生活气息。这是北京城市一个时代的见证。
结语
现代北京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多面体,我们已经很难用单一的形容词来概括其全貌。不过,这也为书写和表征新的北京经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新北京作家群不需要有统一的规范或目标,他们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对北京城市空间感知的拓展,在于对当下北京市民生活的寻觅与凝视,在于对城市时代变革剪影的记录。而正是这种切入当代的自觉意识,才使新北京作家群有了截然不同的亮色。诚然,与老舍等老一辈作家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很难归于正统的“京味儿”,但或许正是区别和差异,才使得他们创造了一种属于现代北京——一个自信、包容、开放的城市——的新京味文学。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许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