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时空与中国古典美学关系紧密,它规约着艺术的形式法则与美学品格。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时空尤其是美学时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总体来看,该研究由最初“求真”的单一模式发展到以“问善”“寻美”为主兼顾“求真”的综合取向,并出现了“时间优先型”“空间优先型”“时空综贯型”三种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问题偏向。中国美学时空研究应统筹兼顾整体与局部的研究范式,同时将时空融会贯通,以此为枢纽,实现多学科的视域融合。中西时空理论之间应展开互鉴互释,这可以为中国美学时空问题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中国美学;时空研究
作者詹冬华,江西师范大学当代形态文艺学研究中心教授(南昌330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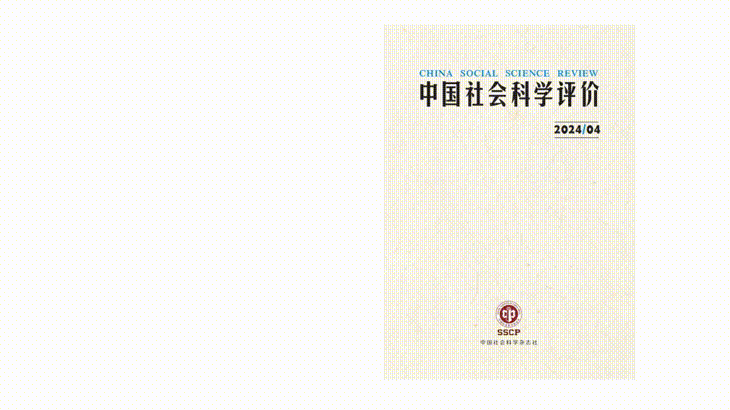
时空是人文学科领域诸多问题的枢纽,也是出入美学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它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化与当代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路径。西方哲学、美学的“空间转向”给中国美学以较大启示。因此,建构并阐发中国美学时空理论不仅是中国美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开展中西美学交流对话,为世界贡献中国美学智慧的重要前期工作。学术界在中国古代时空尤其是美学时空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颇为丰硕,以下主要围绕学术界有关该问题的价值取向、研究模式及问题偏向等方面进行简明扼要的梳理评述,并就后续研究略作抛砖之思,以祈方家教正。
一、价值取向:从“求真”到“问善”与“寻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时空问题展开了全面集中的探究。40余年来,研究的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转变,由科学哲学的“求真”模式过渡到审美文化的“问善”“寻美”模式;研究的重心也由之前的“参照西学”发展为“回归本土”。
(一)求真:对时空本质属性的科学探询
研究时空问题,不可能回避对其本质属性的追问,而寻求古人时空观念的本来样貌,是
时空本属于自然科学关注的问题,从科学哲学角度展开研究非常必要。因此,上述成果具有开拓性意义,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这种“求真”的学术旨趣在后来者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只不过由寻求自然科学之真过渡到还原历史文化之真,即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追溯、还原时空问题的真实面目,这在神话时空、社会政治时空、天文地理时空等的研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王锺陵较早研究神话时空问题,他主要从中国前期文化—心理的角度,结合《山海经》《楚辞》《庄子》等早期文献,对神话中的时空观展开探析,时见新意。此后,叶舒宪充分运用中外有关天文历法、古文字学、地方民俗等方面的文献资料,追寻中国早期神话传统中蕴含的时空观与宇宙观。学术界的后续研究也延续了这种“求真”模式。
“求真”模式也体现在对中国上古社会政治空间、天文地理空间等问题的探讨中。有论者对中国早期的空间规划体系及其重要功能价值等问题展开充分的考辨论述,从更为实证的维度呈现了中国早期空间观的实际应用等情形,具有较大的启迪意义。也有论者以《汉书》所录六种“海中占”文献为基础,考察了“海中占”现象产生的知识史、社会史背景,揭示了上古华夏人的海洋观念及星占学的发展过程,对全面理解中国古代空间观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有意思的是,学术界研究时空问题时,试图在研究手段、方法、目标等方面超出所在学科的阈限,这一点在中国天文考古学、聚落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等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冯时在考察中国古代时空观时,不仅充分调动其熟稔的考古学、文献学、文字学资源和方法,对“观象授时”“盖天理论”“分至四神”“四方五位”“辨方正位”“圭表致日与执中思想”等重要时空问题展开考辨诠解,还延伸至政治、宗教、哲学等领域,阐发其背后的政治制度、宗教观念等文化意蕴。建筑学家张杰致力于中国传统城邑与聚落空间文化的勘察和探究,他从《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神话学、天文考古学、堪舆理论、古代画论等古籍资料和研究成果中寻绎文化线索与灵感,系统考察了中国古代空间文化的主要源流、概念、特征及规律。
随着学术积淀越来越丰富,学术界对古代时空问题的认知更为深入全面,“求真”式研究中自然衍生出“问善”“寻美”的价值诉求。在更为多样的研究理念指引下,人们不再执着于对古代时空的本质及属性等自然科学问题的追问,而是转向对时空与古人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伦理规范、社会心理、审美理想等现实问题之间关系的思考。因此,这时的“求真”由科学哲学问题视域转变为一种客观、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这种精神是古代时空问题研究的压舱石。
(二)问善与寻美:对时空文化意蕴的诗性阐发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时空与政治伦理之“善”、文学艺术之“美”的关系更为紧密。实际上,当学术界将时空研究的视域方法由西方自然科学转向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时,其“求真”的取向自然也带上了“问善”的动机。上述有关神话时空、社会政治时空、天文地理时空的考察,就是在“求真”的同时兼顾“问善”,继而为“寻美”奠定了基础。学术界有关时空的“问善”式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时空的社会伦理价值功用的挖掘,包括宇宙观、时空观与政治文化、伦理观念的关联,阴阳五行时间观与中医学的辩证诊疗,等等;“寻美”向度则聚焦于对时空美学意蕴的阐发,包括传统艺术的时空意识及其美学精神、时间性及空间性与艺术形式的关联,等等。当然,“问善”与“寻美”也可以统一起来,这在宗白华的时空研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
宗白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着手探讨中国古代时空问题,他非常重视《周易》哲学、先秦道家及秦汉的阴阳五行思想,并注意到其所包含的宇宙观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可以说,易学、道论、五行思想是宗白华建构中国古代时空理论大厦的三大基石。以此为理论基础,宗白华对中国古代的诗歌、书法、绘画、音乐、舞蹈等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及美学精神展开了系统深入的阐发。宗白华从功能、关系、生命性、艺术性等“问善”“寻美”的价值维度来理解中国古代时空。这一研究取向对当代美学、文艺学、艺术学等学科影响很大,后续很多有关古代时空的研究就是沿着他的思路和架构展开的,尤其是对诗、文、书、画、乐、舞等士人雅艺形式特征的论析,多受宗白华的启发,将其思想源头追溯到先秦两汉的宇宙观与时空观,但这种学术赓续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才真正实现。
二、重时或重空:美学时空研究的问题偏向
时空难以析离,但在研究中我们可暂时从逻辑上将时空分开,或重视时间,或聚焦空间,或时空综贯,这对研究的推进是便利且有效的。学术界有关中国美学时空的研究出现了三种问题偏向:一是强调时间在时空统一体中的重要意义,认为时间比空间更关键,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美学及艺术的精神旨趣;二是突出空间的优先性和始源性,认为空间表征时间,并对中国美学的本质属性及艺术形式发挥重要的规导作用;三是将时空统一起来,重视二者在美学及艺术中的协同作用。因为关注重点不同,学术界在开展美学时空研究时开辟的问题域也存在差异。
(一)时间优先型
20世纪初,西方的线性时间观进入中国学者视野,对中国古代时空观的现代阐释产生较大冲击。这也反过来激发学术界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时空问题,宗白华开此风气之先。他早年留学欧洲,接触到西方的时空理论,对康德、柏格森的时空理论有较深入的研究。以西方时空观为镜鉴,宗白华指明了中国哲学的时空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同时,他以《周易》为主要思想渊源,提出了“时间优先型”的时空理论:“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
所谓“时间优先”,是指在“时空合一”的宇宙大场域中,时间发挥关键性作用。正如牛宏宝所言,时间意识是审美和艺术的形式动力机制,中国传统文化以“道”为根源,形成了一种“生”与“息”双面体循环的时间观,这种时间意识模塑了中国传统审美的独特方式。“时间优先”理论还辐射到“生命时间”,为传统艺术的美学阐释提供了更为恰切的路径。朱良志从“四时模式”“时空合一”“生命节律”等方面论述了生命时间对中国艺术、美学的深刻影响。
(二)空间优先型
与空灵、抽象的时间相比,空间具有“可居”“可触”“可见”“可象”(想象)等特征,这与古人长于具象性的感悟、思维及话语表达方式相契合。因而,中国古代有关空间问题的言说更为丰富和全面,甚至古人有关时间的理解也借助空间来表达。近十余年来,在西方“空间转向”的激发和带动下,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空间问题表现出很大热情,一方面,继续以西方空间理论为参照,沿用“以西释中”的方法研究古代空间问题;另一方面,在发现自家丰富的宝藏后,聚焦中国古代空间文化,在空间诗学、空间美学、艺术空间理论等方面深入开掘,产出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成果。由此,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空间优先型”的时空研究倾向。
所谓“空间优先”,是指在中国古代宇宙观、时空观的整体构成中,空间比时间更具优先性,空间不仅是时间的表征方式,更是古人的感知经验、思维方式、审美形式的重要依凭,因而在诗学、美学、艺术理论及实践中处于关键性地位。甚至可以说,空间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美学的性质。这一点已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如杨春时提出,中国美学是空间性美学,审美表现为空间性的活动。在诗学方面,邓伟龙从空间维度对诗歌创作的思维方式、目的与追求、创作技巧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系统的阐发。在西方艺术理论中,诗歌一般被看作时间艺术。邓著立足于中国诗歌的文化语境,深掘其中的空间性蕴涵,对中国诗学研究具有补漏填隙之功。
在古典小说领域也出现了“空间优先型”的研究偏向。龙迪勇从建筑群落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小说的空间结构,认为明清文人小说家很有可能从建筑的空间组合模式中去寻找架构章回小说这一“新的”叙事文体的文本结构。因此,建筑空间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形成。也有学者从更为直观的日常器具模型来理解小说的空间性,认为小说叙事场所之间存在“并列”(“板块”)与“包含”(“套盒”)两种空间关系;梅新林借鉴几何学的空间概念对中国古代小说空间叙事进行宏观提炼,归纳出“点”“线”“角”“圆”四种基型。这几种空间叙事的几何基型具有更大的涵盖性,超出了建筑与器具的外在形制,提纯为线条的诸种形态,实际上与中国古代的书画艺术更为接近。
在中国古代艺术谱系中,建筑空间具有奠基性意义。这或许也是“空间优先型”时空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振复从美学角度重点考察了中国传统建筑(包括园林)的空间造型及其形式美感,全面呈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形式特征及其美学意蕴。王贵祥有感于西方建筑理论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及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所持的否定态度,从中西方建筑空间的角度对中西建筑文化传统展开比较分析,以破除西方中心论。
中国古代绘画也是“空间优先型”研究关注的重点。有学者鉴于中西方绘画空间的差异,从中国古代观物法入手考察古代绘画空间,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吴兴明将建筑与山水画所开启的场所空间与图像空间概括为“造物空间”,对其精神内涵与价值指向展开深度解析。
(三)时空综贯型
从学术界已有成果来看,所谓“时空综贯型”研究并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式的平行论证,而是对中国美学、艺术理论中的时空构成及转化关系加以探究。实际上就是将“时间优先型”与“空间优先型”综合起来,更为辩证地考察其中的时空表征及关系问题。如朱志荣围绕中国美学及艺术的时空关系问题展开理论探究,认为中国艺术通过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的方式拓展时空并超越传达的有限性。此外,这一时空综贯的思路也表现在对中国形式美起源的探讨及中外美学品格的比较研究等方面。
从时空角度整体上考察中国传统艺术,须考虑艺术门类的特性及其时空观之间的关系。黄念然概括了“身度”“气化”“节律”“境象”四种艺术时空观,借此论析了中国古代时空一体观对艺术创造的深远影响。杨义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开头多从历史的源头写起,展示出恢宏的时空结构,他称之为“叙事元始”,这实际上是将时空统贯起来考察小说的叙事问题。
上述三种时空研究模式并非固定不变的研究立场和学术主张,而是因问题对象不同所生发的研究重心偏向。因为同一研究者可以采用多种研究模式,并不会株守一隅、胶柱鼓瑟。
三、多元融合:美学时空研究前瞻
综上,前贤的探索为中国美学时空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从多方面启发了后来者的思路和灵感。但由于各人的立场、方法、目的不同,某些观点存在分歧,甚至出现了龃龉不合的情形;由于古代时空问题本身的庞杂性,有些研究踵武前贤,在思维方式、话语表达等方面依傍前贤,往往问题面向逼仄,文献材料雷同,观点大同小异,出现了研究的程式化与知识的重叠堆垛现象。如要实现美学时空研究的整体提升,尚有许多工作要做。笔者认为,中国美学时空研究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做到融合多元视域,刷新研究思维,实现知识创新。
(一)研究范式及视域的融合
学术界在对中西方美学时空进行论析比较时,往往滑入中西各占一隅的思维轨道,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传统重视时间,中国古代注重空间。一旦结论被预先给定,后面的论证就无法逸出这个框架。实际上,中西方都重视时间和空间,只是关注的阶段及方式有差异。中国古代既重视空间,也有非常丰富的时间观念,只要聚焦时间问题,同样可以找出很多支撑材料,得出古人注重时间的结论。“时间优先型”研究便是如此。因此,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时空孰主孰次、孰先孰后,而在于学术研究的现实语境与总体趋向激发了研究者开掘哪个问题域的热情。当多个问题域被渐次敞开后,一种更为通豁、辩证、全面的考察方式也就显得既必要且可能了。
(二)以时空为交集的学科融合
总之,我们需要重新勘察划定美学时空的学术边界,举凡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影响的所有时空方面的思想文化资源均属于该研究的范围。只有这样,有关美学时空问题的研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腋成裘,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实现“美学时空”向“时空美学”的转型升级。
(三)中国时空学说的知识自主
尽管学术界已意识到中国美学时空问题的重要性,也做出了相当不错的成果,但还无法抛开西方理论的“拐杖”,实现学术研究的自立自主。美学时空问题的知识自主有赖于中国时空学说研究的整体性自觉,一方面,应以我为主,兼蓄并包;另一方面,要中西互鉴互释,求同存异。
我们亟待反思的是,中国早期的原创性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庄子等对整个人类的时空思想智慧具有哪些独特贡献?中国古代的时空思想是否具有反向阐释西方的能力和潜质?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古人的思想遗产只有在面向当代问题的开放性阐释中才能释放出潜在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学者应将中西时空理论放在对等的学理层面进行互释,展开对话,寻求思想的契合性,同时也保留各自的文化差异与独特智慧,以实现人类思想文明的互鉴共荣。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