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是声与色的世界,声音与颜色是这个世界的基本要素。古典时期的自然人类首先对两者做了形而上学的沉思,进而在近代欧洲做了科学的—物理的还原主义或简化主义的处理,从而掩盖了颜色显现和颜色感知的其他非科学可能性。19世纪以来的声音工业和电光工业对声音与颜色世界的技术化改造,导致所谓的“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但声音与颜色问题依然成谜。从现象学哲学出发探讨声音与颜色现象可以形成一种“声音与颜色的存在论”,声音的根本问题是“寂声”,颜色的根本问题是“黑白”,无声无色为虚无,而有声有色即存在。从自然人类的具身存在角度来说,我们今天需要维护或者重新唤起一种“听无声”和“观黑暗”的原初感知能力。
关键词: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寂声与黑白;现象学存在论
作者孙周兴,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杭州310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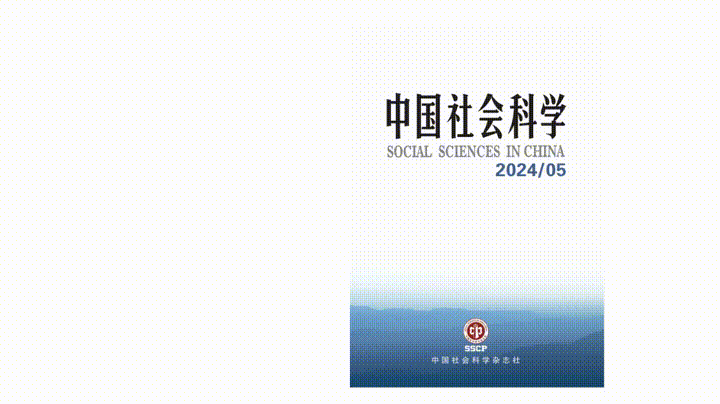
世界是有声有色的
人类的颜色与声音世界是视和听的世界,是感觉的世界。但除了视觉和听觉,人类还有其他感觉样式,即嗅觉、味觉、触觉;故而有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五觉”和佛教所谓的“五尘”或“五欲”,即色、声、香、味、触。基于地缘的自然人类族群文明各有差异,但关于外部世界(自然界)的感觉(感触)以及表达却是大同小异的,可见人有“同感”;这种“同感”似也可佐证康德所讲的“共同感”。
问题在于:在佛教所说的“五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和身识)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五觉”(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当中,为何眼与耳、视觉与听觉具有优先性?而进一步的问题还有:在眼与耳之间、视觉与听觉之间,又为何眼压倒了耳,视觉取得了优势地位和中心地位?
亚里士多德着眼于“本性/自然”(physis)来探讨“五觉”,看起来是比较公正地对待了五种感觉和五种感觉对象,但也许正因为基于“本性/自然”,他对视觉和听觉、颜色和声音的关注是最多的,我们看到,除了《论灵魂》的相关讨论外,还有“论颜色”和“论声音”的专题论述。这就是说,至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世界合乎本性地/自然地首先是有声有色的,是一个声音与颜色的世界。
或问:眼与耳、视觉和听觉的优先性真的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吗?这个问题并不好轻松回答。首先,亚里士多德应该是正确的,在“五觉”中视听的优先性明显具有身体—自然(physis)的基础,或者说具有身体—生理的基础。在动物世界,各种感官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一些动物来说味觉和触觉特别重要,而对另一些动物来说最重要的是听觉,比如我们熟悉的狗,狗的听觉感应力是人类的16倍,它能听到的最远距离大约是人类的400倍;但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眼睛无疑是最重要的感官。
不过,人类视觉机制是高度复杂的。生物学家罗伯特·兰札(Robert Lanza)和天文学家鲍勃·伯曼(Bob Berman)认为,表面看来人类有三个“视觉世界”,一是我们要观看的外部世界,二是在视网膜上呈现的颠倒的视觉图像世界,三是大脑或意识中的视觉王国,即图像被建构和感知的世界。那么,我们到底看到了哪个世界呢?视觉体验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科学的答案是,视觉是由颅脑内的1万亿个脑突触构建的。若然,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至少存在着两个世界,即外部的“真实世界”与我们大脑里独立存在的“视觉世界”?这两位科学家的结论却是相当惊人的:不对,只有一个世界,“视觉图像被感知到的地方就是世界实际所在之处。在视觉之外,什么都没有”。颜色是我们创建出来的,整个可见世界就在我们身体之内,没有所谓的“外部世界”。这个明显违背“常识”的想法差不多接近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了,胡塞尔正是以此理论来解决“外部世界”的存在问题的。胡塞尔认为,意识不是一片空海滩,不是一个有待充实的容器,而是由各种各样的行为组成的,对象是在与之相适合的被给予方式中呈现给意识的,而这一点又是不依赖于有关对象是否实际存在而始终有效的。如果说对象(事物)是按我们所赋予的意义而显现给我们的,那就意味着,并没有与意识完全无关的实在对象和世界“现实性”。于是我们就可以认为,意向意识本身包含着与对象的关联,此即胡塞尔所谓的“先天相关性”。因此,正如德国当代哲学家克劳斯·黑尔德(Klaus Held)所提出的,胡塞尔的“意向性”概念原则上解决了近代认识论的古典问题,那就是:一个起初无世界的意识如何能够与一个位于它彼岸的“外部世界”发生联系。令人惊讶的是上述两位科学家的视觉机制研究竟然在“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上得出了一个与现象学一致的结论。无论如何,现象学的感知理论和意向性学说可以为我们解决颜色感知和视觉机制问题提供一条路径。
其实不光眼睛是精妙绝伦的人体器官,耳朵以及其他感官的演化也是十分神奇的故事。其中完全可与眼睛一较轩轾的当然是耳朵。试问:身体上两个孔的耳朵是如何生成的?耳朵是怎样开始和完成演化的呢?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给出的论证十分简单:人类的任何一片皮肤都能侦察震动,这是触觉的延伸,“自然选择”会青睐特别化的感官即耳朵的演化。按照道金斯的说法,似乎耳朵就是触觉的集中凝聚,而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作为一个坚定的进化论者,道金斯所谓的“自然选择”委实是一把随时可用的“万能钥匙”。不过,面对神奇的眼与耳,我们除了承认自然造化的伟大奇迹之外,夫复何为?
另外,眼与耳、视觉和听觉的优先性也具有社会文化的基础,因为眼与耳在人类社会性功能的实现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而早期人类的两门基础艺术——造型艺术和声音艺术——也加强和巩固了眼与耳、视与听的优先地位。这两门艺术,如果按照尼采的说法就是“日神艺术/阿波罗艺术”与“酒神艺术/狄奥尼索斯艺术”,所谓“日神艺术”不但包括建筑、绘画等造型艺术类型,也包括史诗、神话等文学类型,而所谓“酒神艺术”主要是抒情诗、音乐等。显然,尼采的艺术类型区分依循的也是视听之别。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眼与耳之间,在视觉与听觉之间,为什么眼最终战胜了耳?为什么视觉取得了优先的或者中心的地位?视觉的主动性和外向性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而包括听觉在内的其他感觉方式明显具有消极的和内向的性质。比如在古希腊的历史进程中,视觉艺术与听觉艺术曾经共同生长,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早期文艺可以为此作证。视觉优先性的确立是后来的事,大致是在哲学和科学出现之际(在古希腊就是在苏格拉底时代),从文明样式和媒介上说,是“说唱文明”向“书写文明”时代转换的事。不光是古希腊文明,人类各个轴心文明恐怕都做了一个预设:人类天性向日,是光明的动物。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
在古希腊哲学时代里,亚里士多德关于声音与颜色的讨论最为典型。关于颜色,亚里士多德认为:其一,颜色是可见的东西,视觉对象是可见的,可见的东西要么是颜色,要么是可以用语言说明但实际上并没有名称的东西。“颜色乃是在本性意义上的可见物……”其二,颜色的本质是光,“光是颜色的本质和致使现实的透明物运动的东西,光是透明物的完全现实性”。其三,颜色是光与影的混合,多样的颜色是由于它们分有的光与影的不相等、不均匀。上述三点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三点,即:光与影、明与暗的不同混合,才有不同的颜色。这大概是自然人类的“自然而然的”想法,也是后世科学反对亚里士多德颜色观的基本着眼点。
至于声音,亚里士多德是从物体运动的角度来讨论的,其基本观点是认为,声音产生于事物之间的“碰撞”:“现实的声音是由于某物撞击中介中的另一事物而产生,因为声音是通过碰撞而产生……声音的产生一定要有两个坚硬的物体相互碰撞并且与空气相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声音是一种运动,发声体撞击空气在各个方向发生拉伸和压缩运动,当它碰到障碍时,就像球被反射一样而产生回声。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欧洲近代声学在讨论声音运动时,不再说“碰撞”,而是说“振动”。这种变化或转换是根本性的,因为关于物体“碰撞”的感知是自然而朴素的,而声波的“振动”却已经脱开了自然经验。
亚里士多德的声音论与颜色论已经颇具体系,乃基于自然人类对生活世界的习常感知,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可以说达到了自然人类的感知经验及其表达的极致境界,但显而易见,它未必是“科学的”——并不是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声学”和“光学”,而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科学的声光之学相悖的。
最令人惊奇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叫声”的描述和讨论,值得我们重视,但一直得不到足够关注。亚里士多德认为,并非所有动物都能“叫”,有灵魂的生物才能发出“叫声”。可见“叫”是多么难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引起碰撞的东西是必然具有灵魂的,而且具有某种想象,因为“叫声”乃是一种“有意义的声音”。在我们发出“叫声”时,吸入的空气被用来使气管里的空气撞击气管本身。而这一事实表明,不论我们是在吸气还是在呼气,我们都无法说话,只有当我们屏住呼吸时才能说话。只有人才会“叫”,但人不是乱喊乱叫的;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我们屏住呼吸时才能说话”尤其具有深义,因为在笔者看来,亚里士多德这里关于“叫”的观点已经触及了作为“人言”的语言的起源和发生问题。
世界的声音与颜色当然还与前述的两门基础艺术有关,那就是造型艺术与声音艺术。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开篇就说,在古希腊人的世界里存在着两种基本的自然冲动,两种十分不同的“本能”,相应地就有两个基本的艺术类型,即造型艺术(阿波罗艺术)与非造型的音乐艺术(狄奥尼索斯艺术)之间的巨大对立——按我们这里的说法,也可以说是“色之艺”与“声之艺”的对立。尼采的想法与亚里士多德基于“自然/本性”的声音论和颜色论有承接的一面,但更多地已经悄然完成了一种重要转换,即从古典自然存在论向现代意志存在论的转换,所以尼采说,两种艺术基于两种“本能”,即两种“欲”。
声与色的根本是寂与黑
亚里士多德关于声音和颜色的观点是朴素而天真的,不过其中也不乏深刻和高明之见。“视觉不仅关系到可见的事物,也关系到不可见的事物(黑暗就不可见,但视觉仍能辨认出黑暗)……同样,听觉不仅与声音有关也与寂静有关,前者听得见,后者则听不见……”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地直观到了视觉现象中的可见与不可见、光与暗之二元性,以及听觉现象中的声音与寂静、有声与无声之二元性。但这明显还是不够的,囿于古典存在论/本体论的物观和运动观,亚里士多德的声音论和颜色论尚未能触及声音与颜色现象中所包含的“语言—存在”事件,也即还不能把声音与颜色现象中的“二元性”理解为“语言—存在”的“二重性”发生。完成这一步的是20世纪的现象学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本体论。
海德格尔似乎没有专文讨论过颜色和声音问题,但显然,他已经思入声音与颜色的根本问题了。在20世纪30年代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谈到了颜色/色彩:“色彩闪烁发光而且惟求闪烁。要是我们自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因此,大地让任何对它的穿透在它本身那里破灭了。大地使任何纯粹计算式的胡搅蛮缠彻底幻灭了。”
海德格尔在此首先反对牛顿物理学的颜色/色彩理论,认为牛顿科学(光学)把颜色/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只可能造成颜色/色彩的湮灭,而不可能有真正的颜色感受和颜色经验;进而,海德格尔把颜色/色彩问题置于“存在之真理”的主题之中。所谓“真理”,海德格尔采纳了——更新了——古希腊的“揭示/解蔽”(aletheia)之义。“真理”就是“被揭示状态”或“无蔽状态”。其实这种解说并没有表面看来的那么玄奥。人类日常经验中处处都有“揭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揭示”,即便最简单的感知或直观行为也是一种“揭示”,此刻我在“看”你,我把你“看作”什么,这种“看”和“看作”都是不容易的,其实都已经是“揭示”,也已经是“赋义”。所以作为“揭示/解蔽”的“真理”行为是普泛的、无所不在的。不过,海德格尔所思的“真理”还要复杂得多。只是为了解释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说,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希腊语aletheia意义上的“真理”差不多是一个“双重结构”,既指“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甚至直接把它命名为“神秘”(Geheimnis)——意义上的真理,也即作为“澄明—遮蔽”之二重性的“存在之真理”,是“存在本身”(Sein selbst)的“显—隐”二重性运动;又指“存在者之存在”(Sein des Seienden)意义上的真理,也即作为“天空—大地”——“天与地”——二重性的“存在者之真理”,是可感可知的“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意义世界)的“显—隐”二重性运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真理”的这样一种“层级”区分当然只是为了讨论方便,但不能说有两种“真理”,其实两者是一体发生的。海德格尔又说艺术是“真理”发生的根本方式之一,这种发生其实是“存在之真理”向“存在者之真理”的实现,也即“世界”的发生。“艺术真理”发生出来,才生成了有声有色的世界。
除了颜色,海德格尔同样也把声音置于“语言—存在”之思的玄秘论域之中。我们在此需要重温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中所做的相关玄思,他在其中是这样来描述根本性的“寂静”(Stille)的:什么是“寂静”?“寂静”绝非只是“无声”,在“无声”中保持的只不过是声响的“不动”。但“不动”既不是作为对发声的扬弃而仅仅限于发声,“不动”本身也并不就是真正的“宁静”。“不动”始终仿佛只是“宁静”的背面。“不动”本身还是以“宁静”为基础的。但“宁静”之本质乃在于它静默。严格看来,作为“寂静之静默”(das Stillen der Stille),“宁静”(die Ruhe)总是比一切运动更动荡,比任何活动更活跃。在海德格尔这里,“寂静”并非只是“无声”,不是声响的不动,而是一种真正的动荡,是运动性的“静默”——海德格尔在此用了德语动名词das Stillen(动词stillen的字面意义是“寂静化”或“寂静着”),意在强调“寂静”的生发之义。
由上面展开的“寂静”之思,海德格尔进一步得出了他十分玄秘令人费解的语言观:“语言作为寂静之音说。寂静静默,因为寂静实现世界和物入于其本质。以静默方式的世界和物之实现,乃是区分之本有事件(das Ereignis)。语言即寂静之音,乃由于区分之自行居有而存在。”一句话,语言作为世界和物的自行居有着的“区分”而成其本质—— 这是海德格尔关于作为“寂静之音”的“语言”的基本界说。这话仍然不太好懂,但基本逻辑如同前述的“真理”发生。“语言”也同样构成一个“两层结构”:首先是“寂静之音”,是无声的“大音”,这种“语言”是“本有/存在”(Ereignis/Sein)的运行和展开(二重性/区分之实现),其实已经不能叫“语言”即“人言”(Sprache),而只能叫“道说”(Sage)即“存在”之“显示”(Zeige)。其次是作为“人言”的语言,它同样具有“是”与“不”、“显”与“隐”的二重性运动(区分之实现)。
语言是“寂静之音”。在此笔者想尝试提出“寂声”或者“寂音”概念,或者干脆用一个字“寂”,一方面来简化海德格尔所谓“寂静之音”,另一方面来对应颜色中的“黑白”。因为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声音的根本问题是“寂声”,或者说声音的根本元素是“寂”,那么,颜色的根本问题是“黑白”,或者说,颜色的根本元素是“黑”。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这里使用的“寂声”和“黑白”并不能完全构成一种对应。通过“寂声”一词,实际上笔者是要强调“寂”与“声”的“二重性”,即“无声”与“有声”的“二重性”,或者说“寂”与“声”的差异化运动,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谓“寂静之音”的意义指向;而通过“黑白”,笔者固然也可强调“黑”与“白”的“二重性”,但难以呼应“寂”与“声”。也许与“寂—声”相应的是“黑—色”,与“寂”和“声”相当的是“黑”和“色”。在本文中,笔者只想在字面上强调声音现象与颜色现象的根本性的“二重性”运动,故采用了“寂声”和“黑白”概念。
无论是“寂”还是“黑”,都指向了存在之“隐匿”和“虚无”之境。当代物理学和宇宙学的进展也已经抵达了“寂”“黑”之境,宇宙学家认为,宇宙中的物质多半是“暗的”,只有小部分(5%)是可观察的和可探测的,而大部分(95%)是“暗物质”和“暗能量”,是不可“透视”的,是“未知的”。“任何独立存在的外部宇宙最多是空白的或黑色的。”在现代颜色理论中,红、黄、蓝(一说红、黄、青)被看作“三基色”,也即通过其他颜色的混合无法得到的“基本色”,又被称为“三原色”,它们可以混合出所有的颜色,三者相加则为黑色,又把黑、白、灰三色列为“无色系”。这是科学时代形成的颜色/色彩理论,如今已成为全人类理所当然的“基本常识”,其本质特征是还原主义或者简化主义。而实际上,古典时代自然人类的声音与颜色经验要丰富得多,也要玄秘得多。
在自然人类的经验中,“寂/寂声”和“黑/黑色”都是根本性、本源性的声音与颜色经验。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与欧洲—西方传统有所不同,中国古代讲“五色”,即青、黄、赤(红)、白、黑。“五行”与“五色”相合相应,即:木对应于青,火对应于赤,土对应于黄,金对应于白,水对应于黑。中国古人又有“三色三彩”之说,“三色”为“黑、白、玄”,“三彩”为“青、黄、赤”。在“三色”中,“黑”和“白”明显可解,但什么是“玄色”呢?天玄地黄,此“玄”近黑,黑里带微赤为“玄色”,差不多指示着红黑色域,可谓“玄黑”。古人说的“玄鸟”可能就是燕子,燕子背部之色即为“玄色”。“玄色”作为一种独立颜色是令人费解的。
中国古代的“黑白玄”三色可与西方人说的“黑白灰”三色构成一种有趣的对照。为何中国古代有“玄色”,而西方人讲“灰色”?如果说“灰色”是黑与白之间的“中性色”,那么,“玄色”是类似的中间色吗?此类问题也是大可深究的,但并非本文的任务。我们看到,西方绘画是特别重视灰色的,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曾说过,在你没有画出灰色之前,你还成不了一个画家。当代德国艺术大师格尔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把灰色当作最重要的颜色,尤其是在他前期的“照片绘画”中大量运用了灰色调。里希特自己给出了如下解释:“灰色是一种缺乏主见的表现,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但灰色是我认识自己与表面现实关系的一种手段。”当代德国哲学家彼得·斯罗德戴克(Peter Sloterdijk)最近专门写了一本书来讨论颜色问题,主题却是“灰色”,书名就叫《谁还不曾思灰色?》。
“玄”当然也有“神秘”之义,这种“神秘”之义是与“玄黑”之义相关联的。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这个“玄之又玄”到底是何意呢?怎么来解说之?也可谓众说纷纭。苏辙给出的一个解释是:“凡远而无所至极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极也。”吴澄则明确认为:“玄者,幽昩不可测知之意。”史上此类解说都把老子的“玄”了解为“幽昩深远”,但恐怕还是不够的。只有苏辙言及“其色必玄”,但也只是强调“以玄寄极”,而其他的解说多半放弃了“玄之又玄”者的“玄黑”色义。老子的“玄之又玄”说的是“道”的有无相生,或者说,声音与颜色中的存在与虚无。
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显然直观到了这种“玄黑”之义,并且称之为“幽暗之力”。梅洛-庞蒂这样写道:我说我的钢笔是黑色的,而且我在阳光下看到它确实是黑色的,但这一黑色与其说是黑色的感性性质,不如说是一种从对象中散发出来的幽暗之力。如我们所见,梅洛庞蒂在此上下文中主要讨论的是颜色知觉和颜色的恒常性,但在不经意之间,他已经触及了颜色现象中的根本问题。
我们似乎可以说,无声无色(寂声和玄黑)为“虚无”,有声有色(声音和颜色)为“存在”。从“无声无色”向“有声有色”的生成,在海德格尔那里被表达为“存在—真理”之发生,也是艺术的“无中生有”。
另外,声音与颜色问题也是时空问题。声音与流动相关,是时间性的;颜色与广延相关,是空间性的。于此引发了哲学史上持久的争论。在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依然是从“自然/本性”(physis)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的,他把时间规定为“运动的计量”,“时间是关于前后运动的数”;并且说“时间不是运动,而是使运动成可以计数的东西”。至于空间,亚里士多德没有在“计算”或“计量”意义上来处理,而是在“位置”意义上加以讨论的,是“位置—空间”(Topos)。“空间乃是一事物的直接包围者,而又不是该事物的部分”,“空间是包围物体的限”。亚里士多德那里的时间—空间观点是自然而朴素的,是基于自然人类对声音与颜色世界的基本感知。但我们也要看到,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可以与现代物理学的时间观相贯通,因为它同样基于计量或计算;而他的空间观却与现代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完全格格不入,甚至具有后世现象学的色彩,这也是大可深究的。
近代哲学的时空之争依然落实于视与听、色与声,特别可见于康德与哈曼之争,即哈曼对康德“先验感性论”的所谓“元批判”(Metakritik)。我们知道,康德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把时间和空间内化为主体认知形式的哲学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视为两种“直观”形式,一内一外,时间为“内感官”,而空间为“外感官”,与之相对应的是两门形式科学,即算术与几何学。此时康德信心满满,以为他以此方式已经为这两门“基础科学”做了先验哲学的论证。然而,同时代的思想怪杰哈曼却完全不能同意康德此说,认为时间与空间并不是主体“直观”形式,而是两种“语言”形式,即“听”和“视”,与之对应的也不是两门基本的形式科学(算术和几何学),而倒是两种基本的艺术,即音乐与绘画。这完全是另一种致思路径。哈曼写道:“最古老的语言是音乐,连同脉搏跳动和鼻腔呼吸的可感受的节奏,是一切速度及其数字比例的生动典范。最古老的文字是绘画和图画,它最早地关注了空间的经济学、通过形象对空间的范限和规定。”哈曼早就已经完成了对近代主体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化,而且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语言哲学已经探入声音与颜色的根本问题。在这种对阵中,康德是科学的,而哈曼是艺术的。两者之间恐怕没有对错,但道不同。
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
我们看到,通过对两门基础性的形式科学(算术与几何学)的基础论证,康德的时空观已经是对声音与颜色世界的抽象化—数学化。这一进程早在伽利略和牛顿时代就开始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已经完成了对有声有色的世界的抽离。而通过近代声学和近代光学,这种抽离得以稳步、科学地推进。
近代声学始于17世纪初伽利略对单摆周期和物体振动的研究。伽利略首先发现,振动的速率(即频率)是真正决定发声体所产生的律音之频率的重要因素。牛顿力学把声学现象与机械运动统一起来。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做了一个推理:振动物体要推动邻近媒质,后者又推动它的邻近媒质等,这是声波的传导;声速应等于大气压与密度之比的二次方根。但牛顿此说一直未得到证明。直到19世纪初,克拉尼通过对杆的纵振动和扭转振动的实验推进了对声音在不同媒质中的各种速度的研究。1816年,拉普拉斯指出,只有在空气温度不变时,牛顿关于声波传导的学说才是正确的,声速的二次方应是大气压乘以比热容比(定压比热容与定容比热容的比)与密度之比。
近代光学则开启了关于颜色的物理研究。与亚里士多德的颜色学说相反,牛顿通过著名的棱镜实验证明光谱颜色复合而形成白光,“物体的颜色是由于入射到它们上面的各种光线被不同物体的表面按不同的比例反射而造成的”。这被认为是对亚里士多德颜色理论的根本性颠覆。牛顿的颜色理论第一次对颜色现象做了“科学的”分析处理,主要问题恐怕在于这种理论所具有的明显的还原主义或简化主义色彩。实际上,把自然光还原为七种单色光就是大成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是有争议的。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质疑牛顿设定的七色,认为可分为六种甚至五种颜色。对于这种牛顿式的还原主义或简化主义,梅洛-庞蒂的批评是公允的:“物理学以及心理学给颜色下了一个随意的定义,它实际上只适合于颜色的一种显现方式,长期以来,它向我们掩盖了颜色的所有其他显现方式。”这正是症结所在,今天人类被牛顿物理学意义上的“七色”所控制了,牛顿“七色”已经成了人类的颜色感知模式,而其他多样的颜色显现和颜色感知可能性,则已经被严重弱化,甚至于被锁闭了。
无论近代声学还是近代光学,都具有实验和计算的特征,也即通过实验对声音与颜色现象做数学的分析、抽象、计算。诚如牛顿在《牛顿光学》所述:他的意图“不是用假说来解释光的性质,而是用推理和实验来提出和证明它们”。把声音还原为声波,以及把颜色还原为光波,根本上归属于近代“普遍数学”这一宏大科学计划。这一科学理想在笛卡尔那里得到了最成熟的表达:“谁要是更细心地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只有其中可以觉察出某种秩序和度量的事物,才涉及马特席斯,而且这种度量,无论在数字中、图形中、星体中、声音中,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应该存在着某种普遍科学,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笛卡尔进一步说,这门普遍科学叫作“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在这里,笛卡尔甚至专门提到了图形和声音,在他看来,声音与颜色世界也必须服从“普遍数学”的要求。
18世纪后期开启的技术工业把人类带入非自然的技术存在状态之中,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动摇和摧毁了传统自然人类精神表达和价值构成体系。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是最早洞察到这一历史性大变局的哲人。在1843年的《未来哲学原理》中,费尔巴哈指出未来哲学的任务是“将哲学从‘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导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精神境界,使它从美满的神圣的虚幻的精神乐园下降到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简言之,未来哲学首先要“通过神的哲学的批判而建立人的哲学的批判”。费尔巴哈对旧时代文化的划断和切割主要着眼于宗教—神学批判,但他并未认识到自己的人类学或者“人的哲学”的困难。几年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更进一步,认识到了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技术工业本质,并且断言,因为技术工业的进展,因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至19世纪后半叶,尼采便以“上帝死了”这一著名判词宣告虚无主义时代的到来,宣告主要通过传统哲学和宗教构造起来的自然人类价值体系的崩溃。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尼采的先行者,两者都是一个新时代的先知和一个新世界的预言者。
现在我们可以说,虚无主义也意味着“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或者说,它首先表现为“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
也正是在19世纪后半叶,西方世界产生了声音技术和声音工业。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机械留声机,这台“会说话的机器”令人震惊,意义重大,它开启了人类刻录声音的历史——试想,不可见的、不断流失的声音居然是可以刻录下来、可以保存和复制的,这是何等神奇!自那以后直到今天,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声音记录和存储技术依次经历了机械刻纹(唱片留声机)、磁记录(磁带录音机)、激光刻录(光盘CD机)和半导体存储技术(数字录音器)四个阶段。在此进程中,声音制作和声音传播已经成为现代技术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音乐被扩展和被放大为“声音艺术”,成为技术生活世界的主导文化样式。
与声音技术的产生差不多同时期,也出现了电光技术和电气工业。1879年10月21日,同样是这位爱迪生,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只具有实用价值的电灯。与机械留声机相比较,电灯是一项也许更具历史变革性意义的发明,它使人类终于可能彻底消灭黑夜,把黑夜变成白昼,形成一个“电光新世界”。今天我们已经不难看到,电光是具有技术哲学意义的,是技术工业的突破性标志,可以说对于技术生活世界具有开端性意义,人类由此进入昼长夜短的新阶段,人类终于走出了自然的“火光世界”而进入技术的“电光世界”了。
可以说,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至此方告完成,因为“启蒙”的本义就是“带来光明”和“照亮世界”。这就是说,启蒙运动是依靠电光技术来完成的。此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感性层面,电光技术对于自然人类的事物感知能力的改变和重塑是深刻而彻底的,最明显的一点是自然人类渐渐丧失了对于黑暗和神秘的感受能力。这一改变对于视觉艺术和艺术创造的影响尤为突出,19世纪中期的艺术家瓦格纳已经天才般地预见了世界理性化和透明化进程及其后果,提出“通过艺术重建神话”的策略。
声音与颜色巨变,一个以虚无主义为标识的技术新世界开始了。但我们不妨重复一下海德格尔在《林中路》中的断言: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之际才显示自身。对于声音,我们似乎同样也可以套用海德格尔关于色彩的说法:把声音还原为声波数据,那声音早就逃之夭夭了。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提出“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概念。所谓“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不只意味着世界之变,同时也意味着人性之变、价值之变。这种变化具有二重性:一方面,通过技术工业,由于技术工业的加强和放大,人类成为“声音与颜色动物”,越来越沉湎于“声音与颜色”。有“史”以来,即自然人类文明史以来,今日世界之喧嚣登峰造极,人类纵情声音与颜色的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了。而另一方面,技术工业已经抽空了自然人类的声音与颜色经验,使人类进入“声音与颜色冷漠”“声音与颜色不应”状态之中——尤其是对“寂”与“黑”、对寂然无声和幽暗玄秘的无力不应状态。
在今天的数字技术时代,“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已经拓展和呈现为“数字/数据虚无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信息科学、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学工业”越来越把全球人类带入“数字存在”之中,“数字/数据”成了当代文明和当代生活世界的中心。特别是在刚刚过去的短短三四十年间,人类的三种基本媒介——文字、图像、声音——已经被完全地和彻底地数字化了,速度之快着实令人惊叹。与此同时,这三种业已被数字化的媒介的文化权重和相互关系也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在自然人类文明中,文字是主流媒介,可以说独霸天下,而且一直压制着其他媒介,特别是声音媒介;而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文字媒介和书写文化的地位已经大幅下降了,图像和声音媒介渐入主流,在权重上至少可以与文字媒介三分天下了。而就视觉文化与听觉文化的二元关系来说,在三种媒介中,文字和图像归于视觉,传统纸媒文字和手工图像日益衰落,传统视觉文化样式(文学、造型艺术和哲学等)颓势尽显,越来越寄生于被数字化的文字和图像;比较而言,被数字化的声音显然具有更强大的贮存力和更广泛的传播力,原本被相对边缘化的声音文化已经悄然升起,包括流行歌曲在内的当代声音艺术可以为此作证。正因此,巴迪欧可以断言,音乐充当着关键的媒介角色,我们生活在一个“音乐狂热”的时代。
“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是一个最显著的标志,表明所谓的从自然人类文明向技术人类文明的重大变局——这一变局也被尼采恰当地标识为“虚无主义”。而支配性媒介的转变,也即从文字和图像转向声音,根本上就是从“看”转向“听”,是具有复杂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
听寂声与观黑暗
本文设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描述自然人类古典的原初的声音与颜色经验,揭示由技术工业造成的“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进而尝试从现象学出发探讨声音与颜色现象,形成一种“声音与颜色存在论”。基于自然人类的声音与颜色经验,我们已经指出声音的根本元素是“寂”,声音现象的根本问题是“寂”与“声”之“二重性”,颜色的根本元素是“黑”,颜色现象的根本问题是“黑”与“白”之“二重性”,无声无色为“虚无”,而有声有色即“存在”;而从自然人类的具身存在角度来说,今天需要维护或者重新唤起一种“听寂声”和“观黑暗”的原初感知能力。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无比艰难的任务,因为事涉“声音与颜色存在论”,关乎人类经验中最幽暗和最神秘的部位。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谓的“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并不是一个纯然消极的命名,它指示着一个技术新时代的声音与颜色状态,指示着技术人类的存在二重性,即“具身存在”—“数字存在”的“二重性”(Zwiefalt)。所谓“具身存在”不难理解,无非是指自然人类肉身性的自然存在样式,那么,什么是“数字存在”呢?我们听到各种关于当代数字技术及其效应的表达,诸如“数字化生存”“数字永生”“虚拟存在”“元宇宙”“全球脑”等,而且动不动就有新的表述和说辞,人类似乎已经到了靠创新观念和概念为生的状态。这大概也是“加速主义”时代的必然现象。关于“数字存在”,笔者愿意给出一个初步的和暂时的“定义”:“数字存在”是技术人类状态的存在规定,即在数据当中通过数字和数字关系而得到形式化表达的存在样式。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何谓“存在”(Being, Sein)?因为汉语与印欧语系的差异,特别是古代汉语本身没有形式语法结构(包括汉语中系词之缺失),所以我们对“存在”的感受和领悟有异于印欧语人群,至少在“存在”的形式意义的理解上是有差异的。关于“存在”,伽达默尔给出了基于海德格尔语言存在论的阐释学哲学的解释:“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存在”是语言性的。于是我们可以认为,在自然人类状态中,我们通过“语言”理解和规定“存在”;而在技术人类状态中,我们通过“数字”规定“存在”。而且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欧洲—西方传统哲学中关于“存在”的探讨即所谓“存在论/本体论”(Ontologia)本来就与“形式科学”难解难分,甚至可以说,“存在论/本体论”本身就是一门“形式科学”。
“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之所以不尽是消极的,也是因为已经完成的声音与颜色技术化,特别是声音与颜色数字化过程也带来了一些积极信号,特别是听—看、声—色、声音—图像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视觉中心主义衰落,声音作为传统的弱势样式渐渐取得了某种优势地位。这就在感性论和存在论层面上为克服主体主义做了准备,因为与视觉—图像相比,听觉—声音具有非主体性的或弱主体性的归属意义。看/视觉是主体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暴力性的,所谓主体主义本来就包含着视觉中心主义;而听/听觉则是非主体性的,是接受性的,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视觉主导的主体主义哲学和科学的压制。
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上下文中,美国现象学家莱斯特·恩布里(Lester Embree)写道:“聆听寂静有时候就像观看黑色,而有时候又像观看白色。声音以及颜色都是物体的可观察属性。在黑白和彩色的颜色之间有一种区别,而在寂静和声音之间也有一种类似的区别。但是聆听寂静是最类似观看黑色的,特别类似于在一个封闭空间内的照明被关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黑暗,或者类似于我们在黑夜里把厚地毯蒙在头上的那种黑暗……” 恩布里在此敏锐地发现了声音与颜色之间的一种有趣的类比:黑白(黑色)之于色彩,有如寂静之于声音。我们由此仿佛又回归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声音论与颜色论了。
生活世界是不断生发的声音与颜色世界。这个世界有声有色,是一个“有/存在”(Sein)的世界;这个世界无声无色,是一个“无/虚无”(Nichts)的世界。听觉和声音的根本问题是“寂声”或“寂”(无声);而视觉和颜色的根本问题是“黑白/黑色”或“黑”(无色)。只是今天在技术宰治下的自然人类(末人/后人类)纵情于声音与颜色,不再——不能——关注根本的“无/虚无”和根本的“有/存在”了。作为自然人类,我们的“听”和“看”都成了问题。听力下降,视力模糊,人类垂垂老矣。世界已经太亮,我们失去了感知黑暗的能力;世界已经太闹,我们已经听不到静默寂声。
如何应对?如何抵抗?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给出的一个策略是“倾听”。在阿达利看来,今天我们的眼睛已经趋于昏聩,在建立了一个由抽象概念、无稽之谈与沉寂构筑的现时代之后,我们已不再能预见未来。阿达利建议,我们必须学习多用声音、艺术、节庆,而少用统计数字来评判一个社会。阿达利甚至倡导我们要“倾听噪音”——他显然采取了一个“拓展的声音概念”。阿达利的策略说白了,就是主张“少看多听”。这个策略自然不同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倡议:“多看少思”。
最后让我们又一次回到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总是力求更冷静、更公允地面对这个已成人类天命的技术化世界,在后期的技术之思中,海德格尔向我们——技术人类——提出了两项要求,即:“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在一个技术物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世界里,人类面临一个艰难任务,就是如何应对同一化的、抽象的“技术对象”;而在一个至高神性缺失的计算—数字世界里,我们同时还得重置身位,确认归属,重建技术生活世界的经验。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泰然任之”对应于可见的视觉世界,而“虚怀敞开”对应的是神秘的寂声。前者是行动的“降解”,后者是心灵的“倾听”,是一种重启的“归属”感。所以海德格尔写道:“任何真正的倾听都以本己的道说而抑制着自身。因为倾听克制自身于归属中;通过这种归属,听始终归本于寂静之音了”。这话虽然依然不太好懂,但基本意思是可了解的。
海德格尔的这两项要求——“看”的节制与“听”的专注——当然是连通的,正如他所主张的“诗”与“思”是在“二重性”意义上合一的。于是我们才可以理解海德格尔的下列说法:“对于物的泰然任之与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是共属一体的。它们允诺给我们以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逗留于世界上。”
在“弱感世界”里抵抗“声音与颜色虚无主义”或“声色虚无主义”,维持和重振声音与颜色感知,无疑是未来艺术和未来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而重振声音与颜色感知的根本点正在于“寂声”与“黑白”。于是我们还不得不追问:在今天,“听寂声”和“观黑暗”是否以及如何可能?
结语
声音与颜色问题似乎难以成为哲学的宏大主题,除了少数个案(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牛顿、歌德等那里)和零星的议论,传统哲学史上关于“声与色”的专题讨论不在多数,这就是说,“声音与颜色”是较少被课题化的。“声音与颜色”少受主流哲学传统的关注,根本原因恐怕在于,声音与颜色世界是“感性世界”或“现象世界”,自始就不是传统哲学的主要目标。在欧洲—西方的柏拉图主义哲学传统中,这一点尤为明显。总的来说,声音与颜色现象是无端地受到了冷落的。
然而,如果没有声音与颜色,则世界如何成形和显现?自然人类的文化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声与色的世界,声与色的世界才是丰富可爱的生活世界。分别而言,声音与颜色是多维度的课题,它既是感觉问题,又是艺术问题,更是哲学问题。
首先,声音与颜色是一个感觉问题。在五官五觉中,颜色与声音对应的是视与听,而且视与听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视觉(观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形成所谓的“视觉中心主义”传统。视觉优势或者视觉中心主义既有身体—生理的基础,在欧洲也与起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传统相关。这个传统被尼采称为“柏拉图主义”,它在文艺复兴之后更获巩固,一面表现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视觉对象性—暴力性姿态,另一面也在达·芬奇的视觉理论(焦点透视)中得到了表达。
其次,声音与颜色是一个艺术问题。音乐和戏剧差不多就是“声音艺术”,而绘画等造型艺术可谓“颜色艺术”。在艺术文化史上,“声音艺术”与“颜色艺术”各自的地位、权重以及两者相互关系是变动不居的,并无恒定之态。在古希腊,“声音艺术”发达在先,在前悲剧时代恐怕还有一个“声音艺术”与“颜色艺术”平分秋色的时期,但在尼采所谓“悲剧时代”之后,也即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启哲学和科学样式之后,视觉中心主义便定了型,“造型艺术”就成了占支配地位的类型,加上文字已成为主流媒介,“书写文化”已上升为统治文化,可见出“视觉优势”已经牢不可破了。直到19世纪中叶的“音乐哲人”瓦格纳,这种形势才得以改变,“眼之色”与“心之声”,或者“颜色艺术”与“声音艺术”之间,进入一种新的调整格局之中。
最后,声音与颜色是一个哲学问题。在被称为“柏拉图主义”的观念论哲学传统中,声色感性世界多半是被贬黜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哲学课题。在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对声音与颜色做过专题讨论,他的讨论基于自然人类的朴素感知,可归于后世所谓认识论。在近代哲学中,经验论一派哲学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多半从感觉认识角度涉及声音与颜色问题。除此之外,声音与颜色还是一个时空问题,尤其在康德那里,声音与颜色被内化——被抽象——为“感性直观形式”即时间和空间问题,试图以此为两门形式科学即算术与几何学做一种基础论证。我们也看到,同时代的哈曼坚定地反对康德这种先验哲学套路,主张声音与颜色以及与之对应的听与视乃是语言的方式,从而对应于两种艺术即音乐与绘画。这就意味着,哈曼天才地直观到了声与色的语言存在论之维。要而言之,作为哲学问题的声色现象,至少已经呈现为声色认识论、声色时空论和声色语言存在论。
在今天,声音与颜色之所以成为一个急难问题,还与世界状况和时代处境有关。始于18世纪下半叶的技术工业使人类生活世界越来越疏离于自然状态,造成本文所谓的“声色虚无主义”;在图像和声音被数字化、落入普遍算法逻辑的今天,人类面临更大的难题,因为人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抽象了。如果落实到感受层面,我们正面临一种尴尬的情景:一方面是感觉的技术性加强和扩展,另一方面却是经验的抽象化和平均化。这时候,自然人类的声音与颜色经验反倒弥足珍贵,而且可能更显重要了。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以来的哲学基于对感性生活世界的关注,开始更多地重视声音与颜色问题了。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