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哲学学者、当代文化批评家,韩炳哲从德法古典哲学启航,追溯其写作与阅读脉络,除可近窥其写作技巧和运思方式,更可发现一种自反式的沉浸。无论是政治领域的他者还是审美领域的媚俗,都是他笔下反复出现的主题,由此可以发掘韩炳哲哲学散文中的悖论、敷衍和对根本性问题的视而不见。
关键词:韩炳哲;他者;媚俗
作者安尼,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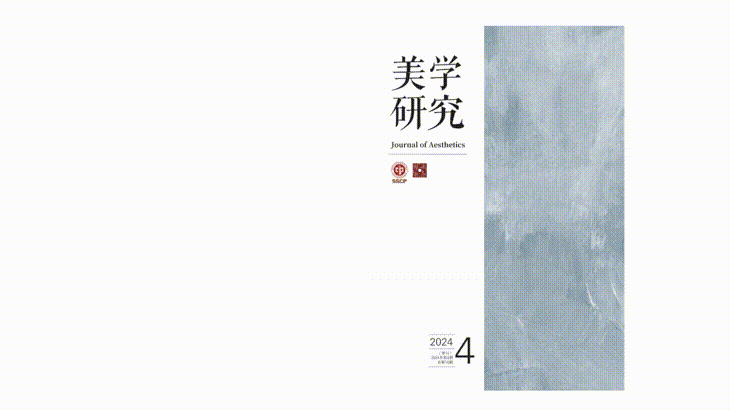
韩裔德语作家韩炳哲不是严谨的哲学家,在他的文字里,抒情与说理平分秋色。从品鉴日本和中国思想艺术的杂文集《禅宗哲学》(2002)开始,到晚近的《叙事的危机》(2023),他以平均每年一本的速度成为罕见的哲学类畅销书作家。除了德语国家的主流媒体,香港《南华早报》、英国《卫报》、西班牙《国家报》《法律与自由》和《美国旁观者》,以及一些小型期刊都对韩炳哲的书进行推介与评论,而这些报刊的主题也超出了通常的哲学范围。
韩炳哲在他的第一部德语作品中,将“空”“无”与“内在性”“实体化”视作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立足于西方视角下对东方的理解,尤其称颂日本文化。在另一部《不在场:东亚文化与哲学》中,韩炳哲继续以日本文化为主导涵盖东亚文化,并一如既往以德法作家对东方的理解为基础,甚至连韩国本土的语言文化——除了在咬文嚼字时举过两个句子外——都被排除在论据之外。罕见的东—西—东的折返视角,加上早期作品形成的小形式文体,奠定了此后二十余年内韩炳哲随笔的写作风格,即便论题扩展到美学和哲学之外的领域。可以说,无论在思想接收还是写作实践层面,韩炳哲都是一个优等生。
小形式文体一度是德语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的中间地带,它融合了时效和个人风格,在100年前十分畅销。许多经典作家也是资深的报刊作者,从副刊写作或纪实报道渐入佳境,走进更广博的写作领域,如罗特、克拉考尔、本雅明。同样是100年前的德语世界,在心理学渐成显学的20世纪上半叶,弗洛伊德的成功也离不开文体的功劳,他的心理学案例分析就像在复述一个个小故事,体量如同短篇或中篇小说,结构与内容完全不像学院派,更像是漫不经心的记叙文。相较而言,无论荣格还是阿德勒,尽管在思想见识和学术影响力上并不逊色,却因文风不够吸引人而无法制造弗洛伊德那样的影响力。于是不难理解,韩炳哲对弗洛伊德的叙事能力赞不绝口,甚至直接认为“理论即讲述”。
鲜明的讲述风格,短促有力的判断句,令他的写作有哲学的坚决,也有散文随笔的飘逸,且跳跃的联想和举述往往效果惊艳。他的确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只是这些小故事更加适合速读,难禁细品。他的叙事更像一部部高级的读书笔记和反思日志,可以给人瞬时的清醒,却无法提供超越性的见识。
01
韩炳哲的阅读谱系遍及哲学、神学、文学、政治学。在哲学层面,他反复援引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唯心主义哲人;在神学领域,他诉诸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或马丁·布伯;在哲学与文学的交界地带,他追溯席勒、诺瓦利斯、克莱斯特、本雅明;而在政治哲学和文化批评领域,他选择施米特、阿伦特、阿多诺、福柯、阿甘本。他并不谨小慎微、步步为营,而是惯于将他们的片言只语作为抒情的顶点,时常模仿这些思想前辈的口吻进行思维游戏,甚至不惜断章取义。这尤其体现在对本雅明和阿伦特的评述中。
韩炳哲的文字敏感度很高,常用非常妙的
除了在《精神政治学》中赫然以政治为关键词,韩炳哲处理现实政治话题的常见方式是欲言又止。在《闭合的仪式》一文中,他以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的《谨慎安置》一文为例说明本土文化与超文化之间的不相容。他当然预感到这样去称颂一个自我封闭的村庄可能会导致怎样的解读。于是,在代入式地与纳达斯产生美学共鸣——引人遐思的野梨树、前现代的共同沉默、去除个体意识的集体仪式——之后,忽然笔锋一转,“不要天真地赞美这里的闭合。如今重现端倪的民族主义蕴含了对那种闭合的要求,也就是排除他者和陌生者。然而,不容忘却的是,不仅全面闭合的否定性是暴力,而且过度开放的肯定性也是暴力,也会招致一种反暴力。”
在这段话中,韩炳哲几次进退,说明他意识到自己的逻辑陷入两难:如何做到在提倡接纳他者的同时,又赞颂闭关自守?究竟怎样的进退才是合理合法?他绕过了这个问题,那冲破古老共同体的动力来自何方?他不去过问。
02
那么韩炳哲的关心指向何方呢?是大众文化与审美吗?是,也不是。韩炳哲对当代最成功的“艺术家”杰夫·昆斯的批评表明:他坚决拒斥庸俗艺术,昆斯就是庸俗艺术家。不过稍作回味便会发现,他的批评只是一段类似微博或豆瓣短评的文字,浓缩了他的诸多基本思想,比如古典与现代的对立、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张力,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却依然只是止于表达不满,甚至令人怀疑,是不是商业上越成功的艺术家就越远离艺术的真正含义?是不是越卖座的哲学家就越远离真正的哲学呢?就像他一样?
韩炳哲的哲学随笔的确充满了艺术的灵动,却少了一丝伦理价值层面的严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震惊与平滑(《美的救赎》《妥协社会》),甚至他所热衷的交流问题(《在群众》《他这的消失》《仪式的消失》)也被戏谑——“杰夫·昆斯是属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家,显得颇有‘智慧’。他的作品表现了平滑的消费世界,对于观看他作品的人,他只需要他们发出一声简单的‘哇哦’。他的艺术刻意让人放松、卸下武装,而且第一要务是讨人喜欢。所以他的座右铭才叫作‘拥抱观众’。他的艺术中没有任何东西使观者受到触动或感到惊恐,正如昆斯所说,艺术是‘交流’。其实他也可以这样说:我的艺术信条是点赞”。
韩炳哲并没有耐心对昆斯的任何作品的特点作简单描述,只是以反讽语气借机巩固对“点赞”、肯定性的抨击。他把艺术效果中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置换成平滑舒缓和震惊痛苦,却不谈平滑、放松、对震惊有意无意的回避这些主观感受的来源在哪里。如果不了解这些心理来源和社会现实的关联,就不可能有行动的勇气。韩炳哲一直绕着艺术理论和思想史上的一个争议性概念转圈,那就是媚俗。
毋庸置疑,昆斯使用传统上被视为“媚俗”的题材,如泰迪熊和儿童玩具,将其吹制成雕塑,并通过当代市场营销策略推广这些作品。其30年前萌生的系列作品《兔子》中的一个版本,是当今在世艺术家中拍卖市场上最昂贵的一个,2019年以9110万美金成交,这只兔子由此也成为维也纳阿波蒂纳博物馆里丢勒的那只兔子之后,世界上最受瞩目的一只。然而,当昆斯在2019年把他最大的雕塑作品之一作为纪念法国恐怖袭击受害者的礼物送给巴黎人的时候,很难说那硕大而鲜艳的郁金香花束给人带来的究竟是震惊,还是安慰和平复。面对这幅作品,大概没有人会跳出来说它媚俗。
那么,评价一个艺术品是否真正具有艺术性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一个作品可以进入公共意识并参与集体记忆,如果它所引发的视觉刺激、情绪体验可以转化成头脑与心灵、理智与想象,那么它是否就能远离媚俗的标签?在商业资本和政治文化空间里,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待艺术品本身?是否排除受众等级雅俗共赏的作品就是媚俗?是否获得巨大商业价值的作品就是对艺术本身的亵渎?这不仅涉及艺术品的形式,更关系到艺术品的社会功能。但这些本可以引发读者头脑风暴和内心震撼的问题,韩炳哲似乎并不关心。
考察媚俗研究史上的代表性观点,可见韩炳哲的审美批评其实非常契合媚俗研究中的一些共识。在20世纪之前,关于媚俗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浮华以及原创性问题。到20世纪之后,媚俗批判一度呈现出爆炸态势。艺术史学家帕佐雷克于1909年在斯图加特举办的展览“装饰艺术中的品味错误”引发当时媒体巨大反响,并激发对媚俗的进一步讨论。他于1912年出版的专著《艺术品的良莠品味》是“试图系统区分媚俗与艺术的最早书籍”。带着其创作时期典型的文化批评和“教育大众”的意图,帕佐雷克主张根据材料质量、实用性和技术以及形式质量来识别“低级趣味”,并将媚俗视为一种“伪装价值”。
德国作家库尔特·马滕斯在1914年出版的文集《品味与教养》中也将媚俗视为一种从根本上建立在不真实和伪装高品质基础上的现象。卡尔·克劳斯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面包与谎言》中,以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痛苦和饥饿为主要特征,对艺术教育和鉴赏的普遍做法提出批评,强调媚俗的“刺激价值”,并承认“媚俗完成了社会满足的使命,能穿透记忆,却不能穿透心灵”。所谓的社会满足,大抵可以置换成韩炳哲笔下的“点赞”。
20世纪20年代,艺术史学家格拉塞提出媚俗的“酸甜二元划分法”,奥地利作家弗里茨·卡普芬指出媚俗是一种“虚张声势,像洋葱一样让人流泪”,并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才能将媚俗消除,而这个改变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本雅明把媚俗看成一个缩小距离的概念,与制造距离、陌生化的艺术势不两立。然而他其实并不清楚媚俗的特征,以及以什么价值标准为基础,这大概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用“光晕”的消失来一边倒地批判机械复制时代的原因。尽管承认媚俗是具有百分之百、绝对和瞬间功利性的艺术,但不同于同时代的人,本雅明认为媚俗创造知识:媚俗如果被正确的接受者(如超现实主义者)使用,就能产生认知联系。
对接受者分门别类,令媚俗显得不那么邪恶,也更具有学术辨析的价值。这个词的贬义色彩在此后几乎没有再得到稀释。1932年,奥地利法学家、心理分析学家汉斯·萨克斯在《媚俗》一文中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分析媚俗现象,并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术语解释说:受压迫的阶级采用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理想,并顽固地坚持这些理想;由于下层阶级在不了解非阶级理想的情况下很难模仿这些理想,因此接受者对定向辅助工具有很大的需求,而媚俗则通过使用各种“不费力就能理解的符号”来满足这种需求,这些符号引导共鸣的可能性“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简言之,媚俗是一种削弱解释和判断力的现象。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理解韩炳哲批评“刻意让人放松”和“讨人喜欢”的原因。此外,这个论断背后还有对接受者来自较低层次的默认。
03
1917—1919年间,赫尔曼·布罗赫在其《认识时代》一书的草稿中首次对媚俗进行系统反思,多年后将这些反思融入一系列文章。布罗赫的卓越贡献是提出艺术的伦理分类法。在1933年发表的《艺术价值体系中的恶》一文中,他认为媚俗就是艺术中的恶,宗教、科学、军事和经济及其子系统都在追求各自的局部价值目标,包括“为艺术而艺术”,而与上帝、美或正义等伟大系统的整体价值目标相距甚远。布罗赫认为媚俗等于邪恶,它恪守陈词滥调,追求个人的情感满足,提供逃进历史田园的机会,是一种从现实到虚构的逃避。
一两百年前的受众已经和知识精英之间形成分水岭。关于移情以及与之相关的情感和情绪批判,席勒早在1791年发表的文章《论比尔格的诗》中就已开始。他认为,与荷马史诗社会相比,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所有社会成员的情感和观点都不再大致相同,因此,“人民诗人”要么只能“让自己适应芸芸众生的理解力,……放弃有教养阶层的喝彩……要么努力通过其伟大的艺术消除两者之间的巨大距离”。席勒将提升人民的道德本能作为诗人的更高要求。艺术家的任务不是放大这个距离,而是拉近彼此从而达到提升大众道德本能的目的,但不是放低自己,而是拉高受众。
如果我们把韩炳哲也当作一个艺术家来看,也许会得出有趣的结论。在2021年《艺术评论》(Art Review)杂志的一个专访中,韩炳哲说他“把哲学当作艺术来实践”。他对当代社会集体症候的分析和批评,时常让人拍案叫绝。而他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为“诗人”中的一个。他用医学术语来剖析暴力和权力的生成和作用机制,令人耳目一新。新自由主义下个人自我剥削的论断,可以让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点头称赞,因为他以心理画像的方式剖析“卷”和行动乏力的内涵。“如果说当今世界不太可能爆发革命,那么原因或许在于我们没有时间思想。”
但是,他却无法促使自我剥削的普通人实现道德提升。读后感式的自我抒发和精辟洞见尽管可以迅速引来喝彩,却不会孵化解决方案。他用前现代的“没有交际的共同体”对抗因社会成员的智识、地位、环境等客观差距造成的散裂与孤立,批驳大数据抹杀个性、曲解真相,可依然不会改变无人能逃脱大数据魔掌以及仪式和礼貌更多在为平滑的人际关系服务的现状。去心理化的呼吁针对的是权力阶层,而韩炳哲的拥趸似乎大多是被心理化的打工人。后者不可能主动去拥抱仪式,放下对点赞和链接的迷恋。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无处获取基本的情绪价值。在情绪价值获得满足之前,道德提升几乎是天方夜谭。
韩炳哲更像是一个布道者,可以点燃一些情绪,唤醒一些意识,引发几场狂欢。他谈点赞的恶,却未对真诚赞美与点赞进行区分;而要对抗新自由主义下的盈利模式或同质化的消费模式,也并不能由沉思或无所事事来完成。他的目光深入现代社会的集体自恋现象,想用仪式制造出的集体沉浸对抗时间感知的无序,却并不能提升大众的道德本能。在触及伦理价值标准的时候,他戛然而止。无论在政治还是审美领域,他都像极了他所批评的博物馆里的观光客和“超文化”里的旅行者。
韩炳哲的哲学散文游弋在自由抒情与逻辑推理之间,优美、轻盈,但缺乏厚重和明晰。在韩炳哲把玩的各种概念中,除了拆解拼贴重新构词,他还会将诸如“新教的”这样受历史条件限定而含义不明的词直接当作形容词来用。如果这个词与马克斯·韦伯放在一起,那么它所指的应该是在资本主义伦理下的那些“美德”;如果与路德联系在一起,那么它是抗议的、世俗化的、自省的。然而无论怎样,这种说法都令人不由想起百年前在政治极权年代流行的那个色彩鲜明的词:犹太的。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问题:在民族争端和领土冲突此起彼伏的当下,对移民问题,韩裔移民韩炳哲先生会怎么说?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