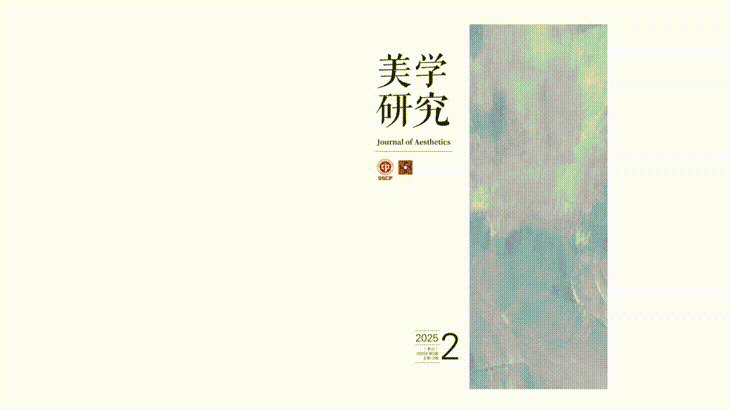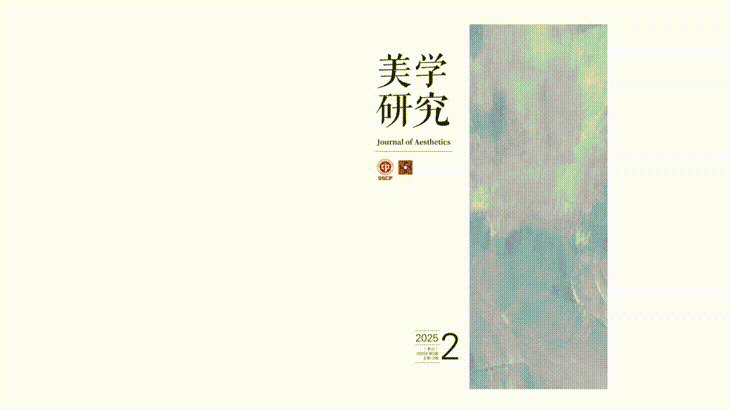
散文是什么?关于散文的定义,在中国古代虽有一个历史沿革的过程,但基本上是与韵文相对应的概念。作为文类概念,散文最早见于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引述周必大的话:“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那么,西方又是如何言说“散文”这一概念的呢?英国随笔作家本森(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曾提出,浪漫派大师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有一句很有启发性的名言:“与诗歌相反的东西不是散文,而是科学;与散文相反的东西不是诗歌,而是韵文。”也就是说“散文”的对立物是“韵文”,这是从“文字技巧结构”来区分的,即韵文是一种“按照某种格律、节奏安排起来的语言形式”,那么散文则应属于此定义外的“语言形式”。显然,这个界定不是正面的诠释,而是采用排他法,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但它恰恰说明散文文类本身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从这一点来看,中西方其实对散文的界说并无大的不同,均强调它是“韵文”之外的一种散体文字。
关于西方散文的起源,按照英国吉尔伯特·默雷(Gilhert Murray)的看法,现存古希腊最早的散文作品,可以追溯至刻在石碑和青铜上的文字。这些文字记载了“一些对公众事关重要的简要明确的文件”。而后,被尊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撰写的历史著作《历史》,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第一个摆脱了荷马(Homer)等人的韵文风格,为欧洲创作了第一部散文文学作品。后来出现的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希腊远征波斯记》等史学巨著,无不体现史家的目的在于“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古希腊罗马时代,大放异彩的是演讲类文章,如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典礼演说,这一切均典型地体现了散文的“实用”功能,同时极大刺激了西方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发达。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散文写作不少源于激起他演说热情的政治与法律问题,其作品的雄辩特点和典雅风格,成为后世追随和学习的典范。古罗马皇帝奥里利厄斯(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带有反思性质,主要思考人生伦理问题;圣·奥古斯丁(S. Aureli Augustini)的《忏悔录》关注自己的精神蜕变过程,是他撰写的一部自传性作品;后来还有法国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的《沉思录》、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忏悔录》均承续这一类反思性著作的余脉。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兴起,一批先觉者自觉运用文艺复兴晚期法国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创立的“Essay”即随笔,作为表达批判性思想的利器,发挥了极大的政治与社会效用。20世纪的批评文论、报告文学更是利用报纸等现代媒介,成为知识者从事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
在中国,散文无论从甲骨文,还是从史官的记录算起,都奔着“实用”而去,体现着中西方散文共有的“实用”功能。然而,细究起来,中西方散文的地位又很不一样。散文在传统中国一直处于显赫地位,其核心价值在于“文载以道”,这个“道”既可以是形而上的,追求天地之理;也可以是形而下的,服务于现实社会,起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作用。无论是曹丕所谓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还是王安石所称“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均是这方面的明证。可是,在西方,散文却因为“经世致用”社会功能的凸显而出现身份认同的焦虑,这是一个特别明显而又复杂的文化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和阐明。
一
纵观西方散文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一些西方学者在探讨散文文体时,常常因其“身份定位”问题而陷入各种矛盾言说或理论困境。
首先,散文的身份。散文虽然“起源于对事实的质朴的陈述”,在“经世致用”方面毋庸置疑,但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起就出现一种“扬诗抑文”的观念,他既被尊称为“诗学”之父,也被誉为“修辞学”之父,不过其内心深处存有一把“艺术”尺子,诗歌与散文被认为有高下之别。他称:
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可见,诗的地位显然高于散文。后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也认为:“散文起于奴隶,寓言这种散文体裁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这是指斥散文出身的卑微。黑格尔即便评价自己比较看好的历史散文和演说散文,也呈现出复杂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认定“这两种散文在各自的界限之内是最能接近艺术的”,另一方面又斥责“连最完美的历史著作毕竟不属于自由的艺术”,“演讲术尽管有这种表面的自由,却仍在最大程度上受实践方面的目的性规律的管辖”。即使到了20世纪,西方对散文的艺术定位仍然不高。这不禁让人好奇,在西方的艺术门类中,散文为什么一直处于边缘和尴尬境地?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认为,这要从散文作家对“自己工作的态度”中寻找缘由,他们把散文视作“一头卑微的役畜,只能去干各种各样零星的杂活”,把散文视作“不洁的物质,任由尘埃、小树枝、苍蝇混杂其中”。即便他们抱有“一个实际的目的——他要为某个政府争辩,他要为某项事业辩护”,也会“采纳道德家的观点——悠远的、困难的、复杂的东西都得抛在一边”,“使用最简单的语汇,尽可能清晰地表述自己的意思,把信息以最浅显的方式传达到尽可能多的读者那里”,“一旦传递出自己的信息,像其他完成使命的物品一样被扔进了垃圾堆”。其实,有同感者何止伍尔芙,美国散文作家怀特(E.B.White)也说:“我并不奢望随笔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占有位置——它毕竟不登大雅之堂。随笔作者,与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不同,必须满足于自我设定的二等公民身分。”由此可见,这种贬低散文的情形在西方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归根到底是西方知识者对这一文类的认识有偏见。
其次,散文的跨界。《大英百科全书》在诠释“非小说性散文”时提出,“试图给非小说性散文规定一个单一的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定义都有其局限性,或者是排除了精髓,无法适应非凡广阔、多样的文学现象”。由此观之,不能给散文“下定义”的尴尬,是由于担忧其规定“单一的特性”会排除文类的“精髓”,认为它无法适应“非凡广阔、多样的文学现象”,这实际上道出了散文存在文类的“跨界”现象,凸显出散文这一体裁的活跃和不稳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部文体类别的多样化特征。对此,加拿大学者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提出:
散文与韵文的不同之处,在于散文还可用于各种非文学性的用途:它不仅能达到文学的边沿“韵律”和“场景”,而且还能扩展到外在世界的“实践”或“行动”和“理论”、社会活动以及个人的思想。
显然,散文与韵文相比,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可以用来表现各种“非文学性的用途”,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它的外延不断扩张,其文类边界也越发模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陈述“非小说散文”在西方的“跨界”现象:
它采取的形式有政论、辩论、传记、自传、宗教经典、普及哲学和伦理论著等。16世纪起更兴起一种私人文体,即用书信、日记、忏悔录等形式作多少带有些掩饰的自我表白和自我解剖。此外还有格言、虚拟对白和历史记述等。再后又出现了新闻报道和其他小品文章。19世纪许多作家不满足于丰富的创作想象力,还借序言、回忆、小品文、自白和评论等为他们的作品进行解说。现代作家,不论诗人、小说家还是剧作家,他们写的非小说散文一般都多于诗歌、小说和剧本。
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开出一份经典书目:柏拉图(Plato)《对话集》、塞内加(Seneca)《致卢西留书简》、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多恩(John Donne)《布道文集》、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形而上学的沉思》、帕斯卡尔《沉思录》、狄德罗(Denis Diderot)《百科全书》和《哲学思想录》、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Schlegel)《断片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格言式作品、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附录与补遗》、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的虚构日记等。
我们会发现散文以其敏锐的触须和柔软的身段,穿行于各种文类之间,由此获取、分享、统摄其他文类的种种可贵品性,呈现出“蔚为大观”的跨界现象。一方面,一些人欣喜地发现一大批诸如《圣经》、柏拉图的《对话集》、帕斯卡尔的《沉思录》等通常被排斥于文学之外的“巨著”,突然获得一种“新的文学方面的意义”。即便是那些原先困惑于如何处理由圣·奥古斯丁开先河,并经卢梭而确立其现代典范的“忏悔录”文体的学者,由于意识到这些“忏悔录”具有“不同的散文形式”,而使“一些散文体名著佳作在虚构文学中明确获得一席之地,而不至再搁置于难以归类的杂书堆里”,学者们可以不必再为它们能否编入宗教或哲学类著作而纠结和懊恼。另一方面,如果将那些宗教经典、普及哲学和伦理论著都当成散文文类,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文类归属的困惑。因此,如何把握好分寸,形成一定的判断尺度,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和难题。诚如卢卡奇(György Lukács)所说,如果只是一味热切地强调散文(论说文)这一文类的纯文学性,可能没有抓住要领,但如果仅以为“写得好的就是一件艺术品”,那是否表明“一则写得好的广告或日常新闻也是文学创作了?”
最后,散文的艺术评价。在散文的艺术评价方面,西方学者经常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散文既然是用来指涉口头的和文字的叙说,起源于对事实的质朴的陈述,这就意味着散文的艺术追求和审美表现有别于韵文。有学者提出:
散文不象被我们称为“韵文”的那种文体那样被组织在周期性重复的韵律单位里——识别种类繁多的非韵律语言——根据各类语言利用节奏感的程度和形式构成的其它表现方式,来确立非韵律语言的范畴——是大有裨益的。这个范畴的一个极端是无规则的、偶尔正式的一般性述说。
韵文的语言形式在于它有“周期性重复的韵律单位”,而散文对应的自然是“非韵律语言的范畴”。然而,“非韵律语言”是一种无规则的范畴,当然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语用特点——无论它的功能是描绘、说明、叙述或表现——那就是“质朴”。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散文的风格美在于“明晰”,“既不能流于平凡,也不能提得太高,而应求其适合”,“只有普通字才能使风格显得明晰”,“在散文的风格里,只有普通字、本义字和隐喻字才合用”。如此一来,这种“少文崇质”的智性追求,还让一些西方学者将“prose”(散文)与“prosaic”(散文式的、平庸乏味的)这两个词的语源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自然就倾向于认为散文存在不少弊端:其一,散文“平庸,散漫”,而且“难以补救地平铺直叙,缺乏精致”;其二,极其常见的散文(随笔、小说、短篇故事)的外观“予人以内容充实和连续的感觉”,较长的散文“常遇到的危险是重复”,作家“在散文作品中常常安排并重复若干线索”;其三,散文作家坦承“他的作品中的某部分只起着次要作用”。
正如前面所述,西方学术界倾向于将散文看作有目的性的、记述和写实性的文类。因此,他们在将散文与诗作比较时,往往态度鲜明。例如,法国象征派诗人瓦雷里(Paul Valéry)把散文与诗的区别比喻成“走路”和“跳舞”的不同,走路是“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但“走路毕竟是一种比较枯燥的、不容易达到完善的行为,而跳舞这种新的行为方式,却可以有无数种的创造和变化或花式”。可见,西方学术界无论将散文比作“一头卑微的役畜”还是“走路”,均是不把散文当作纯艺术门类的心态的流露,其间产生矛盾叙述或陷入困惑境地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
不过,面对散文“身份定位”的困惑,西方学者也曾致力于探讨摆脱困境的方法和措施。亚里士多德说:“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也不应当没有节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散文有了“格律”,就会没有说服力,还会分散听者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没有“节奏”,也就没有限制,这样一来,散文就不讨人喜欢,也不好懂。而古罗马的西塞罗发现,在早于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时代,希腊人就会运用“对句”,称作“antitheta”,对立的观念在其中并列,由此在散文中产生“格律”。因此,他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提出“散文中的格律”问题。在西塞罗看来,格律不是现成的,它与散文没有必然联系或亲缘关系,它后来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带来的东西就像运动员优雅的训练,给散文风格添加完善的格调”。散文让人印象不佳,诸如出现“一段话拘谨、支离破碎,一段话随意、到处扩张”等,“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不是文字的性质,而是排列在一起的、长短不同的、语词的间隔”。因此,让散文产生“这些间隔的交织与混合,有时候稳重,有时候快速”的现象,“必定取决于格律”。西塞罗为此详细探讨了长短短格、短长格、派安格三种格律的运用形式,并且提出散文可以“派安格”作为主要尺度,应当使用“混合的格律”来驾驭,体现出兼容的态度。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地位显赫,其散文的格律主张和创立的拉丁散文标准对西方后世散文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学者提出:“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到十八世纪,在英国散文背后有着拉丁文的模式。”其实不止于此,“18世纪以来,西塞罗散文雄辩的特点和典雅的风格一直是许多英国文学家学习的典范。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事实上,我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塞罗的影响。”对此,雷·韦勒克(René Wellek)和奥·沃伦(Austin Warren)将这种散文模式称为“节奏性散文”,并勾勒出这一散文谱系的发展脉络:
在英语文学中,节奏性散文的鼎盛时代是十七世纪,出现了布朗爵士或泰勒(J. Taylor)这样的散文大家。十八世纪英国散文变成了一种更简洁的口语式文体,到该世纪末甚至出现了以约翰逊、吉朋和博克为代表的一种新“雄浑体”。到了十九世纪,节奏性散文在德昆西、拉斯金、爱默生和麦尔维尔的作品中以及斯坦和乔伊斯等人变化的形式中获得了复兴。在法国,有波苏埃和夏多勃里昂的辉煌散文体;在德国,有尼采的节奏性散文;在俄国,果戈理与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有不少著名的节奏性散文片断,晚近则有巴依里(A. Byely)的“装饰性”散文。
这似乎充分说明了拉丁语散文不仅在西塞罗时代及其后的罗马帝国,以及漫长的中世纪占有绝对统治地位,即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进入近现代社会后,它仍然以其独有的韵律和典雅,深深影响了西方散文向节奏清晰、音韵和谐、语言绮丽的一路发展。
当然,西方散文还有另一条发展路向,古希腊罗马时代不仅有亚里士多德主张散文的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以及追求散文风格的“明晰”,还有塞涅卡主张:“语言注重的既是表达真理,就该简洁明了,朴素自然。”卢奇安(Loukianou)也认为:“也许你们散文家就不能夸夸其谈,俗语有云:‘半升米用不着大口袋’。”这一观点也得到近现代西方学者的回应和共鸣。德国语言学家洪堡(W. von Humboldt)认为,散文的萌芽和发达与人民的智力水平密切相关,古希腊散文建立在古希腊的精神之中,“精神产生散文的需求”,即“在智力的自由和财富中,已经有了产生散文的需要”。同时他提出:“语言在有文化的人民处于智力下降时被精神——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的繁盛都只能仰仗于这种精神——所遗弃,那就绝对产生不出伟大的散文;而如果精神的创造变得平庸、变为学术上的收集,则散文便衰败。”“诗歌只能属于生命的某些时刻,只能属于精神的某些情调;散文则与人长相随,出现在人的精神活动的一切表露之中。散文趋就于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感受;它在语言中通过确切性、明晰性、灵巧的生动性、悦音与和声的训练而得以提高,获得可从任何一点出发腾达于自由追求的能力。”而英国学者艾弗·埃文斯(Ifor Evans)则从散文服务于现实的效用出发,认为:“考虑到衡量事物的标准是生活而不是艺术,那么一个国家的散文就比它的诗歌重要得多。”又称:“一国人民对于他们的立法者、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最高要求,是一种不装模作样、不含含糊糊和不加渲染的散文。”基于这样的认知,艾弗·埃文斯将批评锋芒直指古罗马以来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拉丁散文传统,他说:“英语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矫饰的散文,通常使人想起它所受拉丁文的影响;而另一种较简朴的散文,则接近于一般本族语的节奏。”由于拉丁文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崇尚“简朴”之风的散文并不是特别受到青睐。
然而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来临,这个局面慢慢发生了质的变化。当然,改变的原因是欧洲各国本土意识形态和民族语言(方言)的成长。正如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 Hartman)所说:“一个更具历史性的出发点定将是文学语言、竞争性的民族语言的成长,这种语言在现代对抗着并取代了拉丁语。在每一个国家中,意识形态的发展是多么复杂啊!”“改善方言、赋予方言以尊严,并把它们提高到普遍性水平”,甚至成为17、18世纪一些国家建立研究院所确立的目标。因而,叔本华说:“人们书写的语言就是人们的民族面相。”所谓“民族面相”,自然是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将《圣经》“从一种死了的、似乎已经埋葬了的语言,译成另一种还没有活着的语言”。前者指的是拉丁语,后者指尚未形成的“德语”,而马丁·路德《圣经》的译本语言“在短短几年中便普及到全德意志,并被提升为共同的书面语言。这种书面语言今天仍然通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和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上的统一”。从这个意义说,马丁·路德创造德语,同时也开创了德语的散文。
在英国,16世纪的学者已经“在铺平承认英语为标准的表达工具的道路”,但尊崇拉丁文仍然是上流社会的主流风气,《随笔集》作为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传世之作,其语言还是拉丁文,他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散文作家”,竟不相信英语语言会有永久性,这真是一件颇有“讽刺意味”之事。但随着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国散文开始迎来一个崭新的开端。德莱登(John Dryden)等一些散文作家开始在英国散文里谈论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私人琐事。18世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创办的《评论报》使撰写报刊文章成为亲切宜人的工作。而后这项工作在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和约瑟夫·阿狄生(Joseph Addison)手上又得到了极大的开拓和发展。阿狄生自信地称:“有人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我不自量力,愿意让人说我把哲学从私室、书库、课堂、学府带进了俱乐部、会议厅、茶桌、咖啡馆之中。”从此,英国散文开始走入普通读者之中,成为那个时代一种便于使用的工具,成为文学部门中最为发达的一种文类。
尽管如此,切莫以为拉丁语已经淡出欧洲人的视野,走向了消亡。其实,它已经变成欧洲人文化血液中的一部分,融进了现代欧洲每一个国家的语言之中。有学者就提出,对他们来说,没有拉丁语言,“就像没有头颅的肩膀”,真正的学者是“那些脚上被戴上脚镣却仍然要读柏拉图的人”,就其本身的高贵优雅来讲,“拉丁语言具有不朽性”,“罗马仍然是永恒存在的”。单就语言的运用而言,散文呈现出多种风格并存的复杂局面,因而,对于承载不同语言形式的散文艺术,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
由此观之,西方散文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发展历程,但只要抓住散文游走于“实用与艺术”之间这一特点,就可以对西方散文的起源、多元共生的跨界现象,以及艺术评判的挪移与变迁等复杂的学理问题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梳理和总结西方学者为了改变散文的“身份定位”而作出的种种探究与实践。西方散文或趋于典雅绮丽,或奔向明晰简朴,尽管这两种路向泾渭分明,但同树异枝,彼此系连,最终演化成一种盘根错节的散文文化现象,呈现出西方散文文类内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范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