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卧游”是中国古代美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经历代学者发微,涌现了宗炳的卧游畅神观、郭熙的卧游快意观和吕祖谦的卧游怀想观。程正揆以卧游为核心而创作的《江山卧游图》系列作品及其相关画论,既兼具上述三种卧游美学的基本特征,又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程正揆对于幻境山水的阐发,进一步丰富了卧游美学的内涵与深度。
关键词:卧游;江山卧游图;程正揆;畅神;幻
作者章含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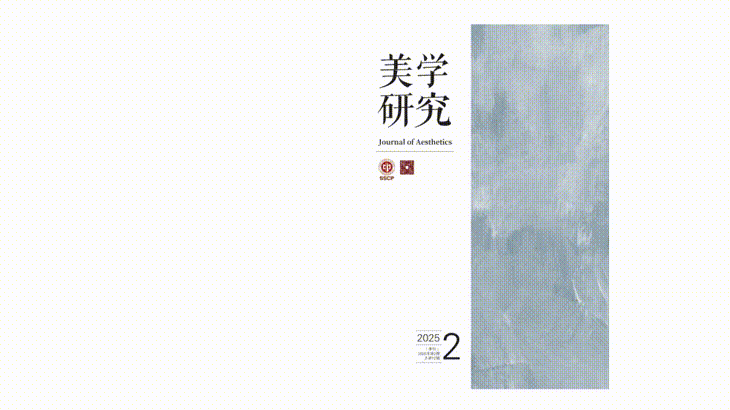
程正揆(1604—1676),字端伯,号鞠陵,别号清溪道人、青溪老人与青溪旧史。程正揆是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画家、绘画理论家,与他的好友髡残并称“二溪”(髡残号“石溪”),其艺术造诣颇得当时画圈认可,龚贤曾用“逸品”来定位程正揆的画作。作为画家,程正揆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工程”莫过于《江山卧游图》系列作品的创作。此系列作品多达五百余卷,现存世的三十余卷《江山卧游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
一、传统卧游美学的三个取向
在展开论述之前,笔者想先澄清的是:尽管“卧游”是文人雅士笔下的高频词汇,但此概念最初与美学不甚相关,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行实践而出现的。先秦时期,《文子》中有“暗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谓大通”的说法,用以描述圣人的状态——圣人达乎大通,没有分别之心,“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仿佛镜子一般,不会被成见、情感与欲望所蒙蔽。从外显形象来看,圣人犹如饮了醇酎,酣畅甘寝,但以内在维度观之,圣人已然忘形遗累,抱道含和。后世学者在解读这段话时,也多将此句与《庄子》的“逍遥乎寝卧其下”“孙叔敖甘寝”关联在一起,使“卧”带有了较强的形而上学意味。东汉时期的存思、守一等道家养生术,进一步明确了“安枕而卧,神光自生”的修行之法。
至宋朝时期,随着朝堂稳定,卧游的受众逐渐从宗炳这类山人隐者拓展至了士大夫阶层。士人们久居都城,忙于政务人情,几近绝缘于山水,但是他们又存在着追求心灵自由、精神解放的现实需求,于是借着山水画而“卧游山水”的行为成为儒臣名士接触山泉林石的重要途径。郭熙于《林泉高致》中指出,君子身处太平盛世,肩负着忠君与侍亲的现世义务,如果像隐士那般孤身自好,那么在处事节义方面就难以周全,所以对于士大夫而言,山水画不失为一种“不下堂筵”就能“坐穷泉壑”的替代方案,其能有效地协调君子林泉之志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让士大夫们心生“快意”之感,不再“芜杂神观,溷浊清风”。
不过,士人对于卧游的态度不局限于寻求精神快意,有时还紧紧地绑定着政治情怀,吕祖谦的《卧游录》便呈现了这一点。与宗炳相仿,吕祖谦也晚年患疾,卧病在家,受卧游精神的感召,每当在书中读到前人关于记载风景名胜的文字时,吕祖谦便会命门人摘抄下来。吕祖谦离世后,后人将其书抄辑录成《卧游录》。关于“卧游”,吕祖谦曾在写给南宋政治家周必大的尺牍中写道:
近书新衔谯、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福,兖之太极,华之云台,皆可卧游也。此虽戏语,使四方无虞,鳏寡废疾者得自佚于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
卧游的畅神观、快意观与怀想观是中国古代卧游美学的三种基本类型。通常而言,每种卧游都对应着特定的受众群体。程正揆的身份较为特殊,他在明清两朝都有过为官经历。尤其是在第二段仕途中,身为明朝遗民的程正揆在清廷体验了从平步青云到罢官返乡的大起大落,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程正揆的艺术创作,因而其《江山卧游图》中的卧游思想既杂糅了以上三种卧游观,又体现了程正揆独有的个人风貌。
二、以山水自娱:程正揆的卧游快意观
程正揆出生于明朝末年的官僚家庭,其父程良孺与画家董其昌交好,因而程正揆幸运地获得了后者的亲炙。董其昌非常喜欢程正揆这位年轻的后学,“凡书诀画理,倾心指授,若传衣传钵焉”。尽管在绘画上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早年程正揆还是与大部分读书人一样,以求取功名为重。凭借着天资聪慧,程正揆在孩童时代便能下笔千言,并于21岁考中举人,28岁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然而,一身骨鲠的程正揆很快便遭受了猜忌,根据姜绍书的《无声诗史》记载:“主爵者忌其才,中以考功法,调之外任,当补幕僚。”但程正揆不屑出任,直至1642年前后才官复原职。
在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之际,程正揆奉命去南京公干。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程正揆只得投奔福王朱由崧的南明朝廷。1645年,清兵南下,朱由崧弃城而逃,程正揆在赵之龙的率领下,迎清军入城,归顺清廷。为了巩固政权,清军入关之后招募并重用了不少汉臣。在这个背景下,此后十年间,程正揆官运亨通,1649年,程正揆赴京上任,担任光禄寺寺丞一职,后历任光禄寺少卿、大理寺寺丞、大理寺少卿、太仆寺卿,直至工部右侍郎。顺治皇帝喜好文艺书画,于是在督修乾清宫期间,顺治皇帝“命以画进”,将程正揆召至瀛台,“给笔札命画,上喜,又召写屏十二幅。”
程正揆仕途春风得意,实现了政治抱负,不过随之相伴的是身居朝堂高位,终日忙碌于人情世故,无暇顾及自己的逸趣雅好。程正揆曾自陈为官期间“戒诗十余年”,其子程大皋也说程正揆“四十以后,居长安中,诗文皆废”。程正揆迫切需要在功名利禄与精神自由之间寻求一种协调,以缓解其中的张力,重获身心快意,于是创作山水画成为程正揆的首选。
起初,程正揆大多以“自娱”的心态作画,把卧游当成公务生活之余的调剂。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两点。其一,画师能“到访”因各种原因而无法前往的景点:
补足迹之不及到。或山阿阻隔,或时事乖违,或艰于资斧,或具无济胜,势不能游而恣情于笔墨,不必天下之有是境也。
其二,画师又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审美心境去领略山水之美,无须顾虑旅途中的风险或疲惫。毕竟在当时,虽然旅游行为开始频繁起来,但交通物流、配套设施和安全保障远不如今日这般完善,出游是存在一定危险的:
大凡游山者,多失之疏脱,失之草率,穷日则疲,畏险则却。虽有奥渺,咫尺悬绝,以倦眼对,残晖成厌物尔。贤者亦不免也。卧游必无是事。
程正揆卧游山水的事迹传开之后,立刻出现了求画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程正揆开始意识到,卧游并不是自己独有的爱好,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共有的需求。于是,程正揆慷慨地把画作分享给朋友,特别是那些懂山水画的、“胸具有丘壑者”的知音。程正揆也萌生了创作《江山卧游图》系列作品的想法。在《题赠舒五公卷》中,程正揆明确地袒露了自己的动机:
居长安者有三苦:无山水可玩,无书画可购,无收藏家可借。予因欲作《江山卧游图》百卷,布施行世,以救马上诸君之苦。
这一时期,程正揆的创作数量也从几幅到“三十余卷”“六十余图”,再至“近二百卷”“三百幅”,直至五百余幅,“间或作画自娱”变成了助他人一起卧游和寻求快意。程正揆的《江山卧游图》系列之所以如此抢手,切中士人的“内在需求”自然是重要原因,但如果撇开“内在需求”而从“外部视角”来庸俗地看,作品的走俏离不开彼时程正揆身居高位,正获得清廷的赏识。不过也恰恰是这份名气,给程正揆带来了许多争议。有的求画者索图无果后,便开始造谣程正揆“以画媚人”。为此,程正揆奋起自辩:
臣未尝以画示人,人亦不知臣画。若画可媚人,窃恐媚于人者弗受也。
言下之意,若自己的画作真能起到谄媚人的功能,或许别人也不敢收受。然而,这段自白并没有平息争端,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危机,即御史张自德的上书弹劾。程正揆因纵酒挟妓、行为不检而被弹劾。在清朝,官员挟妓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根据《大清律例》规定:
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亦坐此律。)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文承荫,武应袭。)宿娼者,罪亦如之。
对于这项罪名,暂无史料表明程正揆是如何应对的。我们只是知道没过多久,程正揆就被罢免官职,返乡青溪了。公允地说,程正揆的仕途受挫与其自身行为失范显然脱不了干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当清廷入关并站稳脚跟之后,开始清理程正揆这类明朝贰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程正揆的遭遇可谓是时势使然。不过,对于艺术创作而言,这个变故反而为程正揆之后的卧游美学带来了重要的转变契机。
三、绘造化山水:程正揆的卧游怀想观
仕途失意与黜官返乡给程正揆带来了不小的打击,虽然他以“丘壑置宜此子,温柔乡足为侯。一榻半窗坐啸,扁舟五湖漫游”的诗句来自我开释,但是对于深受忠君报国、“学而优则仕”传统熏陶的中国古代士人来说,程正揆的贰臣经历显然既不光彩也不成功。因此,“京师十年,如蚕之处茧”《“灰心功业非侯骨,弹指乾坤此老身”的无可奈何才是其真实的内心写照。
回归青溪后的程正揆拥有了大量游历山水、从事创作的时间与闲暇,似乎不必再像为官时那样借助卧游来获得快意,然而若从创作《江山卧游图》的数量上来看,退隐之后的程正揆反而更加注重卧游(当然,注重卧游与亲历山水并不矛盾。根据其子程大皋的说法:“二十余年来,遨游吴越之间,沉酣书画,江山之胜,悉具胸中”)。1658年春,在《题〈江山卧游图〉》中,程正揆提到了自己创作时的一件趣事。公远质疑程正揆的画作,称其“江景不类”,即画中景色与现实山水存在着较大差异,对于这番指摘,程正揆回应:
造化既落吾手,自应为天地开生面。何必向剩水残山觅活计哉?且沧海陵谷等若苍狗白云,千年一瞬也,安知江山异日不迁代入我图画中耶?
言下之意,画师作画与自然生成相仿,都是一种造化行为。既然如此,画师的任务就未必是去严格“还原”自然景物或规律,而是应当用笔墨绘制出自己心目中的事物风貌,呈现出世界的另一番可能秩序。于是,程正揆大胆地在绘画中拉长了时间尺度,试图把海桑陵谷的事物变迁和白云苍狗的世事无常都纳入画作之中,为《江山卧游图》赋予生成流变之感。应当注意,这种绘图方式明显有别于程正揆《书〈江山卧游图〉卷后》里的观点:
天地是一幅大山水,人却向画中作画,何异梦里寻梦耶?然造化有人工,万物设色纤微,皆化境,非笔墨所能描写。人夺天功,手腕开辟,窃恐天地未必胜画工也。人天各有长处,相适政以相成,能通乎其间者,可与言绘事矣。
由于没有落款时间,我们无法直接给出《书〈卧游〉卷后》的成稿年代,但可以明确的是,落笔《书〈卧游〉卷后》时的程正揆认为,绘画不能只以画师笔墨为准,否则无异于“画中作画”“梦里寻梦”,失了真实。在程正揆看来,自然世界的纷繁细节不是人工笔墨所能穷尽的,相反,画师的巧思妙笔,亦能在画卷中呈现出别于自然的独特景致,换言之,人工与天地皆有自身长处,画师唯有在师法自然的同时不为事物所役,实现“相适政以想成,能通乎其间者”之境界,才是最为理想的创作状态。程正揆在《题画十五首》诗句里的“江山如画画如真,墨妙玄工各有神”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不难看出,画师究竟应该与“天地相适”还是“为天地开生面”,成为界定程正揆《江山卧游图》不同时期风格的重要标尺。可问题又接着来了,为什么题于1658年的《题〈江山卧游图〉》会如此强调造化山水而非“人工与天工的互补”呢?笔者认为,原因或许有二。
其一,现实山水的凄凉景象。明清换代之际,战火连绵,从明末的农民起义,到清军入关,再至清廷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近四十年的战乱把青山绿水生生地变成了残山剩水。按照程正揆的说法,“兵火连仍,今昔迥别,山川城郭,举目都非”。面对这样的破败场景,难免让人“怆心特甚,有何托兴?使人踟蹰”。
其二,程正揆郁郁不得志的心境。程正揆曾赠诗于陈名夏(陈百吏),两人皆在投降清廷后被委以重任。对于清廷一开始的重用,程正揆在赠诗中感慨:“故国遗元老,新朝重旧人。自难雕朽木,非是积前薪。斗酒浇诗磈,秋风振剑尘。暮砧催落日,古道一归臣。”可以看出,此时程正揆对未来是踌躇满志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萌生了“全躯点圣朝”的想法。然而当程正揆因朝堂纷争而落寞归乡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终究只是位客乡人,所以即使“投身新雨露”却也“满眼旧江山”,这份惆怅的心情在“短发天涯客,寒心故国霜。向君询往代,何以对潇湘”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既然现实的山水与人事如此不堪,那为什么还要在其中寻求慰藉呢?毕竟“去国日以远,涛声夜不同”,还不如凭着卧游去重新造化山水,然后“买醉寻乡曲,移舟入画图”。《一旦接受了这重视角转换,那么无论是程正揆亲眼见证的这十余年朝代更迭,还是百余年的王朝兴替,抑或千年文明演变,皆为万古历史长河中的短暂一瞬而已。无怪乎程正揆诗曰:“石纳千帆影,山留万古春。文章扶世界,天地报才人。江韵何曾歇,松风故自淳。不知桑海后,庙貌几回新。”在卧游山水的过程中怀念故土、放下故土,最终进入历史的形上遐想,此即为程正揆的卧游怀想观。
四、寻幻境山水:程正揆的卧游畅神观
造化山水是程正揆主动地、有意识地把内在心境投射于外在山水,以寻求官场失意与人生逆旅的释怀。然而,这种卧游怀想观是以否定不如意的当下为前提的。倘若程正揆真想做到“山色故自变,云心淡若凝。随风随作态,一雨一番奇”这般洒脱,那么他似乎就需要对现实予以更多的接受和宽容,而这正是程正揆在《书〈江山卧游图〉卷后》中展现出的卧游新特征,他说:
程子住青溪之上,二十有五年。升沉仕路,如上竿之鲇;生死患难,如归城之鹤。其间晦明风雨,嬉笑哭泣之事,不啻蜃楼蝶梦之几千万状也。返观诸相,总是一画图尔。天地为大粉本,摹拟不尽,可谓化工无劫数矣。然有山崩川竭,陵谷海桑之变,岂天地亦画中幻境耶?吾辈拈七尺管,任意随笔,可使十洲三岛聚于一毫,琪树恒河成于俄顷,章亥不足步,五丁不足驱也。人力固胜天地耶?予作《卧游》卷若干,又是画中作画,孰幻孰真,以俟具眼能超三界之外者鉴之。
当然,这种卧游境界并不是随便就能获得的。除了画师必须拥有学识、经验、技法等基本素养之外,程正揆还着重提及想象力与记录梦境。此处的想象力,主要是指文本层面的想象力。宗炳与郭熙论及卧游时,大多围绕着山水画展开,吕祖谦虽把卧游体验拓展至文字,但其《卧游录》大多为辑录前人游记,并未告知世人如何循着文字去卧游。程正揆开创性地阐明了文本想象力如何助力于卧游体验,他说:
文字到传神处,妙在于景象全不相似却逼真,在卧游者细心理会尔。心与眼会,方觉山水文章真精神面目一齐托出。
卧游时既获名胜,复赏奇文,诵读之,想象之,反覆摩拟,身入岩壑,松风、泉响悉合耳根,渐引入非非想天,奇情异境,溢于山水文章之外,不可思议。此何状哉!内典所谓“带影识从无明来”,即是开辟天地种子。嘻!幻哉!
程正揆指出,想象需要基于优质的山水文本,其行文不必复刻自然,但须把握景象的内在神韵,并能与景象“相互映发”。在反复诵读、揣摩和体味的过程中,读者逐渐想象出自己亲历风景时的具身感受,从而领略山水文章背后的真精神。文本想象不是无源之水,势必会激活读者曾经游历山水的体验,想象与经验最佳的结合情形,莫过于“偶一触动,状态幻出,妙在若忘若忆,若合若离”。
除了借助文本想象力之外,程正揆还异常珍视自己的做梦体验。在《青溪遗稿》最后一卷《奇梦录》中,他专门记载了自己一生所做的各类奇幻梦境。程正揆认为,梦境值得关注是因为:
人之有梦、犹天、地、日、月之有影也。弦朔晦蚀,由影而成。凡物之精灵,非一不神,无两不化。乾坤之昼夜,人之梦觉,乃错综变化、参赞位育之大橐、大键,不可忽也。所以异于禽兽草木者几希尔。高峰和尚入死关三十年,只了得梦想中事;庄生凌驾万物,尘埃野马,目不一瞬,蝴蝶栩栩,如斯而已。梦之义大矣哉!予生平多奇梦,想耶,因耶?有无耶?遂记于左。
晚年的程正揆对道、释颇有研究,在他看来,睡梦与清醒一样,既是世人生命的组成部分,也是个体生长的关键因素。世人往往在乎清醒的状态,却没有意识到梦能以一种区别于醒的方式,更加直观地洞悉到“人生天地、宇宙万物都是幻梦一场”。在梦境之中,“一刹那顷可历恒河沙,无量数劫庶得梦语三昧”。程正揆认为,正是由于高峰和尚、庄子对梦都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才能参透生死,故曰“梦之义大矣哉!”
通过梳理,我们业已呈现了程正揆卧游美学中的三重内涵。首先,程正揆为官时以卧游来平衡政务生活和精神自由,从而实现身心快意;其次,黜官回乡的经历使程正揆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贰臣身份,在心灰意冷之际用造化山水替代现实山水,从而卧游于怀想中的历史形上空间;最后,程正揆真正地接纳了人生羁旅的种种遭遇,意识到如幻无常或许才是世间真相,故而运用想象与梦境来模糊虚实边界,在醉梦体验中卧游山水,以期精神畅快。程正揆热衷卧游山水,其曲折的生命历程导致他的卧游美学杂糅着卧游快意观、卧游怀想观与卧游畅神观,我们难以从中抽拉出一条贯通的义理脉络。不过,也恰恰是这份杂糅,给程正揆的卧游美学带来了鲜明的层次性和历时性,帮助我们认识到,卧游不仅仅是一种审美体验,更是美学思想与人生际遇相结合的产物。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胡海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