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虚构悖论”是20世纪90年代广泛讨论的美学问题,但作为争论起源的拉德福德未对其中的信念问题作出完整的解答。根据以往的观点,“悖论”存在的矛盾在于,我们既能对虚构角色或处境产生情感,同时又相信这些角色或处境并非为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沃尔顿试图通过讨论信念来说明,我们在面对虚构作品时其实是在玩一场“假装游戏”,并处于一种“假装相信”的状态,因此在其中产生的情感并非完全真实的情感。此外,虚构角色不仅出现在传统的虚构作品中,还会出现在各类游戏中,其中独特的“化身”给予了虚构角色更多的讨论空间。同时,对于信念问题的再讨论,也将给予一个面对虚构世界的清晰视角。
关键词:虚构;假装相信;情感;游戏化身
作者李香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2488);孙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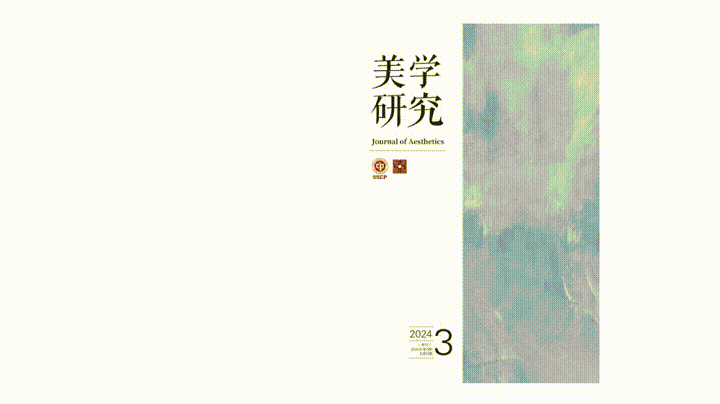
拉德福德(Colin Radford)在其文章中提道:“似乎,我只会被某些人的境遇所打动——如果我相信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某人身上的话。而倘若我并不相信某人遭受过或正在遭受这些事情,我就不会悲伤或被感动到落泪……而这种想法意味着信念。我们必须相信有人遭受着痛苦。”这一说法引起的主要分歧在于:如果要让我们对某些事物产生某种情感,我们必须持有对应的信念,即相信其为真;而面对虚构作品,我们会对其中的事物产生某种情感,并且同时相信这些事物是虚构的。两者显然是彼此矛盾的:对于前者来说,产生某种情感的必要前提是相信某事物为真,而对于后者来说,即使事物是虚构的,我们仍然会对其产生相应的情感。于现实世界而言,对某些真实对象产生真实情感是符合直觉的。然而,于虚构世界而言,我们会为小说、电影和游戏中的虚构对象落泪,好像也有着与真实无异的情感。两种情形中的情感都是真实的吗?我们又如何会对虚构角色产生真实的情感呢?我们是否只是将这种情感“误认”成了真实的情感?
一、如何解决虚构悖论中的信念问题
为了解决这对矛盾,有必要先从“虚构悖论”这一问题的源头着手。亚奈尔(Robert J. Yanal)在其文章中将这一“悖论”总结为三个命题,并认为这三个命题无法同时为真:
(1)我们能对一些虚构作品中的角色和情形产生情感;
(2)即便我们相信那些角色和情形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我们也能产生这些情感;
(3)仅当我们相信角色和情形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们产生情感。
亚奈尔指出,拉德福德对于这几个命题的态度是接受“(1)”和“(2)”,即当我们相信对象是虚构的,我们也会对这些事物产生情感。倘若接受“(2)”和“(3)”,那么就会得出我们既能在相信对象是虚构时对它们产生情感,同时又不能对它们产生情感,这显然是矛盾的。拉德福德在其文章中提道:“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会被艺术作品以某种方式打动——尽管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并且只在这种方式下更容易理解,但这却会让我们陷入不协调和不连贯的境地。”他似乎得出了一个较弱的结论,即我们之所以会被虚构作品打动,原因在于某种非理性。无论如何,拉德福德的结论并不能让人满意,至少将结论归于非理性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仍然需要从根本上进一步说明“虚构悖论”。
从本质上看,“(2)”和“(3)”的主要冲突有二:其一是反实在论和实在论的不相容,其二是情感概念的模糊。在虚构问题上,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实在论承认存在实在的虚构对象,反实在论则认为不存在实在的虚构对象。倘若我们以实在论的立场进行讨论,那么无论虚构对象以什么形式存在,人们面对存在的事物产生信念都是符合直觉的,因此需要着重论证的是虚构对象本身的特殊存在方式。相对于实在论,反实在论实际上处于较弱的辩护处境,原因在于支持实在论的理论较多。然而,反实在论在澄清信念问题上有着独特的方式,因为对虚构对象产生信念是一件极其矛盾的事情,至少,面对虚构对象产生的信念和面对真实对象产生的信念不能混淆。因此,在此问题上沿着反实在论的路径进行分析更具潜在可能。
在反实在论方面,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提出了一个例子来对“悖论”进行改写:
查尔斯正在看一部关于绿色史莱姆的恐怖电影。当史莱姆缓慢渗出,无情地吞噬着地面,摧毁了沿路上的一切时,他整个人缩在了椅子中。不久之后,一个油腻的脑袋从泥浆中冒出来,镜头就定格在了两个珠子一般的眼睛上。此时,史莱姆的速度越来越快,从另一个方向渗出来涌向观众。查尔斯发出一声尖叫,并绝望地抓紧他的椅子。事后,查尔斯颤抖地承认,他受到了史莱姆的“惊吓”。
在这样的立场下,沃尔顿实则对“(3)”作出了一些改写:
(3*)仅当我们完全相信角色和情形是真实的而非虚构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们产生真实的情感。
这般改写的必要在于,“(3)”实际上并没有将面对现实世界的情感与面对虚构世界的情感区别开来,而这就会误将两类情感混为一谈。查尔斯并不满足“相信其为真”的前提,对此,沃尔顿的论证形式大体如下:
P1. 仅当我们完全相信角色和情形是真实而非虚构的时候,我们才能对他们产生真实的情感;
P2. 我们无法对虚构的角色和情形产生真实的情感;
P3. 因此,我们无法完全相信角色和情形是真实而非虚构的。
与“相信其为真”不同,查尔斯实际上的态度是“相信其为虚构”,这意味着相信对象是虚构出来的(这与虚假不同);而“相信其为真”意味着倘若某人声称某事物为真,那么暗含两种态度:一是相信该物现实存在,二是相信该物为真。其中,前者无关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立场,仅仅宣称某对象为非现实,而后者无疑拥有着实在论的倾向。当我们在故事结束后听闻其是编造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对于该故事的态度便是“相信其为虚构”,这意味着这个故事是非现实,但没有宣称任何和实在性相关的内容。
假设存在现实事物R1,那么“相信R1为真”实际上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R1在现实世界的实在地位。而假设存在虚构事物R2,那么“相信R2为真”实际上也会产生赋予R2实在地位的意图。而无论怎样,“相信其为虚构”并无赋予实在的意义,而这也是沃尔顿反实在论立场的一个温和之处。对此,沃尔顿认为,我们对这些虚构出来的东西采取“部分相信”的态度似乎是更为合适的——他将这种态度称为“假装相信”(make-believe)。“假装相信”意味着讨论某种“虚构性”(fictionality),从而暂时搁置了实在性问题。但是,这种做法是一种妥协,给沃尔顿的理论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此外,沃尔顿也对“(1)”和“(2)”进行了改写:
(1*)我们能对一些虚构作品中的角色和情形产生与真实的情感相类似的情感;
(2*)即便我们相信那些角色和情形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我们也能产生这种类似的情感。
如此,改写后的“虚构悖论”便能使得“(2*)”和“(3*)”同时为真,因为两个命题声称的情感种类并不一致。根据沃尔顿的观点,我们面对虚构作品产生的情感无法完全和真实的情感相提并论,否则我们理应有完全相同的情感反应。由改写过的三个命题可以得出沃尔顿对虚构之中的信念问题的基本结论:假设存在一个虚构故事f,我们只是假装相信f为真,而实际上我们相信f是虚构出来的。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欣赏虚构作品时无需任何真的信念?
塞恩斯伯里(R. M. Sainsbury)对“假装相信”有过一个很精辟的解释:“在消费虚构作品时,消费者通常只是假装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尽管她对此并不相信它为真……这些(面对虚构作品的)反应应该受到一种规范的限制:仅当故事中说了p时,才假装相信p。而这与信念的真理标准相对:仅当p为真时,才相信p。”结合两人的描述,“假装相信”意味着将用于信念的真假判断“暂时搁置”。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假装相信”这样的信念,是因为这是参与虚构世界的必要。对此,沃尔顿将这一切都描述为一场“假装游戏”(game of make-believe)。
二、我们在游戏中假装相信什么
沃尔顿在查尔斯模型之外,还举了一个树桩与熊的例子:
有一个和熊十分类似的树桩,可以让一切看到它的人将其想象成熊,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其他人也会进行如此想象。如果这个自然形成的树桩不太有熊的样子,那么就需要刻意地进行雕饰。但是,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法可能是,如果我们事先给予一个指令或约定(比如,“让我们把树桩称作熊”或干脆说“看那头熊”),那么就能让树桩指导我们进行更具体的想象。
在这个例子当中,把树桩当作熊的做法可以看作一场“假装游戏”,树桩在这场游戏里承担着“道具”(prop)的作用,能使参与这场游戏的人都把树桩当成熊。“道具”概念的引入可以进一步解释先前提到的“虚构真实”:在树桩与熊的这一假装游戏当中,“树桩是熊”为真,这是因为这场假装游戏“授权”(authorize)我们可以进行如此这般的想象。有了这种事先规定之后,游戏的参与者都会遵循这样的规则。
根据沃尔顿的说法,一些艺术作品也可以被视为道具(如绘画和电影),能促使我们进行某种想象,参与艺术欣赏也是在参与一场假装游戏。查尔斯看恐怖电影实际上就是在参与一场假装游戏,电影本身便是道具,其中的史莱姆就是由此生成的虚构真实,这场假装游戏“授权”我们假装相信史莱姆存在。查尔斯本质上是在对所生成的虚构真实感到“恐惧”,这意味着他在假装相信这种虚构真实,而当电影结束即假装游戏结束后,这种“恐惧”就消失了,参与者没有必要继续对其中的虚构真实感到“恐惧”。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沃尔顿对这种“虚构情感”的进一步说明:在假装游戏中,我们不会对生成的虚构真实产生完全真实的情感,而只会产生类似的情感,这种类似的情感只会在这场游戏中维持。但是,这一理论较为紧急的问题是:如果查尔斯的恐惧并非完全真实,那么要如何解释许多人在观看恐怖电影后仍然会“后怕”呢?难道游戏实际上还在继续吗?这或许是虚构世界让人信以为真的关键所在,在假装游戏结束之后,人们在现实之中有时很难辨别这种“后怕”到底是真实情感还是准情感。在此,不妨先探讨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之所以会如此令人信以为真的可能论证:
P4.人们面对现实世界x会产生情感q,面对虚构世界x*会产生准情感q*;
P5.情感q与准情感q*并不完全相同;
P6.如果现实世界x和虚构世界x*存在相似性,那么情感q和准情感q*也存在相似性;
P7.事实上,我们往往会从虚构世界x*联想到现实世界x,这意味着x和x*存在相似性;
P8.因此,情感q和准情感q*存在相似性。
其中,判定准情感与真实情感类似的一个重要根据在于,我们能否将现实世界x和虚构世界x*也看作类似的:查尔斯之所以会对史莱姆产生类似的恐惧,可能源于他对某种现实中类似的情形会产生真正的恐惧(例如,查尔斯会对现实中的黏液产生恐惧)。这个论证并非沃尔顿明确提出,但却能说明该理论的重要疑点:区分准情感和真实情感的理由太弱了。沃尔顿更多地从具有生物性质的情感反应程度来进行区分,并且将准情感和真实情感的对象分别设立为虚构对象和真实对象。但是,倘若我们以反应程度来判定情感类别,那么现实中也存在情感反应较弱的反例,有时甚至弱于面对虚构对象时的反应。总而言之,沃尔顿单纯用反应程度来区分两类情感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并且,我们又要如何认为某个准情感q*会有真实情感q与之对应?或许沃尔顿在此处有着某些潜台词,即准情感中有某种因素使得这种反应有些“不足”或有所“缺失”,但遗憾的是,沃尔顿并没有清晰地指出这种因素。一种较为激进的解释是,基于反实在论的立场,这种因素并非实在性相关的因素,而更应该是某种独属于虚构对象的因素,即某种“虚构性”因素。这种“虚构性”源于虚构世界而非现实世界,这意味着面对两类世界产生的情感虽然在表面上类似,但实际在根本上就存在差异。但是,沃尔顿实则倾向于温和的反实在论立场,这种边界清晰的情感区分并不符合他的预期——至少,两类情感在本质上还有着相似之处。
此外,沃尔顿试图将这种情感诉诸心理状态和某种经验:
关于查尔斯生成的虚构真实,一部分由他的思想和感觉,以及他的实际心理状态生成。一部分是,他经历了的准恐惧、感觉心脏剧烈跳动和肌肉绷紧等事实使得他在害怕成为虚构的……
如果我们接受沃尔顿的这个说法,那么似乎就能说明这种“后怕”:查尔斯在观看恐怖电影时产生的只是一种准恐惧,然而,当电影结束之后,他仍然担惊受怕,这是因为他想到了曾经看到过的一种绿色黏液,使得他感觉自己有危险而产生恐惧。因此,查尔斯真正恐惧的是现实当中曾见过的和史莱姆类似的东西,他有过如此这般的情感体验,所以当他在电影院联想到了那种真正令他恐惧的黏液时,才会在电影院产生准恐惧q*。
然而,不仅仅是查尔斯,许多观众在看完一场恐怖电影时,往往也会产生“后怕”,难道他们也都通过电影回想起了那种真正令他们恐惧的情形吗?恐怕沃尔顿的说法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在这个问题上,实在论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某人没有对史莱姆产生真正的恐惧,也没有在现实之中对类似的东西有过真正的恐惧,他所恐惧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
从实在论角度来看,当谈论虚构世界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将其视为一个可能世界,并且可能世界为真,其中虚构对象也为真。但是,沃尔顿基于反实在论立场认为,虚构世界并非实在的,其中的虚构对象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真”(例如,相对于现实世界,福尔摩斯住在贝克街在对应作品所在的虚构世界中为真)。同时,虚构世界在实在论立场下是真实而非现实的,这意味着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有本质上的差异。此外,沃尔顿倘若要以可能世界的路径解释“后怕”的类似情形,那么除非他以温和的态度宣称“假装相信”能给可能世界以反实在论地位,即可能世界是一种相对的真实并且不承诺虚构对象的实在性,否则可能世界在其反实在论立场中难以自洽。
另一个问题在于,假装游戏是否能够延续?在树桩与熊的游戏当中,参与者会假装相信树桩是熊,而倘若在游戏结束之后,参与者在其他地方看到了类似的树桩,并下意识地将其想象为一头熊,我们是否能够将这场假装游戏看作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进行?这涉及一种与“游戏规则”相关的想象:授权或允许参与者假装相信树桩是熊,而不是想象成另外的东西。因为在游戏过程中,有规则使我们如此这般想象,而游戏结束之后,这种规则对于想象而言就是不必要的。也就是说,想象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会将游戏继续进行下去:例如在游戏中,我们可以将树桩想象成熊,也能将树桩想象成老虎,但倘若我们接受后者,那么树桩与熊的游戏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而是会转变成树桩与老虎的游戏。
所以,沃尔顿的理论在这里也不太完全适用,且不论可能世界本身是否能在反实在论意义上自洽,假装游戏本身能否延续也是存在疑问的。这是因为假装相信和想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需要游戏中的授权,后者则不需要,更何况游戏本身的规则在游戏结束后没有继续对想象给予规范的必要。这也证实了先前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实在论和可能世界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而沃尔顿的解释并不支持假装游戏的延续。总而言之,我们的确会想象与“作品世界”(world of works)类似的虚构世界,但除非规则仍然作用在后来的虚构世界,否则我们无法将两者视为同一场假装游戏,也无法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看作延续的(事实上,脱离了虚构作品的想象往往是任意的)。
不过,将面对假装游戏产生的情感看成沃尔顿意义上的准情感是可行的,但要注意的是,游戏结束后的规则和先前的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实在论者和沃尔顿对于“后怕”的解释不同,前者会将“后怕”看作一种真实的情感,后者则将其看作一种准情感,这本质上是双方的理论分歧。沃尔顿结论较弱的地方也在于此,他对两种情感边界的说明仍然是模糊的。但不管怎样,这里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虚构作品,倘若要继续将沃尔顿的理论运用到现实世界,那么还存在的问题在于:对于现实世界的对象,我们是否会产生并不真实的情感?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说明虚构世界何以令人信以为真,那么仍需要解释,当脱离虚构世界之后,我们为何还会不自觉地假装相信?或者说,为何对游戏的规则念念不忘?
三、参与者和游戏化身
倘若如沃尔顿所说,那么好像我们对虚构作品就从未有过真情实感,但是,这一理论仍然存疑。沃尔顿实际上认为,我们有着两套相互类似而又存在差异的情感模式,即面对现实事物我们会有相应的真实情感,而面对虚构事物则会有相应的准情感。但是,且不论沃尔顿在两者区分上的弱论证,这种相对独立的划分是否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这种特殊的准情感似乎不仅仅发生在对待虚构的情形中,还发生在体育比赛之中,沃尔顿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观看戏剧的时候,你会为英雄喝彩,为坏蛋叫骂。你会“关心”其中喜爱的角色,并希望它们更好。观众会在罗密欧和朱丽叶面临悲剧结局时感到不佳;一些人甚至流下泪来。同样地,体育迷会为自家的队伍喝彩,或者为他们“喜欢”的队伍或队员喝彩……
沃尔顿在后来的文章中将虚构作品和体育赛事进行了比较:在体育赛事当中,同样有着和那些读者相类似的观众,但此时观众的情感对象是真实的队伍和队员,观众为真实对象的胜利感到喜悦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沃尔顿点明了其中的关键之处:
这些粉丝是不理智的吗?……许多体育迷就像故事的读者,是在其他方面理智的人,知道什么重要以及什么不重要。一些人会告诉你,如果你把比赛放到一边,打破比赛的魔咒,那么谁赢其实并不重要,或者至少没那么重要,这会让他们看起来没这么在乎。很多人在比赛之后就会将其迅速忘却,而这对于那些看起来对比赛很关心的人来说太快了……
他观察到,在比赛中产生的情感是一种短暂的情感,而这与面对虚构作品的情形有所类似:虚构作品的观众在欣赏结束之后,尽管情绪还未消停,但仍然知道其中的结局和命运是已经被决定好的,他们对此没法改变。但是,这些队员和队伍又有什么命运和结局可言呢?我们可能事先知道两支队伍的实力悬殊,并坚定地认为某支较强的队伍会获胜——但事实上,体育比赛中的“黑马”并不少见,以弱胜强的戏码偶尔也会发生。比赛中产生的短暂情感让沃尔顿注意到,假装理论好像并不单纯是虚构作品的专属。在体育比赛中,观众好像也是在进行一场假装游戏,不过其中的对象并非虚构的,反而是真实和现实存在的。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将这种竞技体育也看作一种特殊的虚构:体育迷和虚构作品的观众一样,比赛是一定程度上不影响现实的事情,因此同样可以看作一场假装游戏。但是,这并没有破坏沃尔顿的反实在论基础,因为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承诺虚构对象的实在性,而只宣称假装相信在现实对象面前也同样适用,这样一来,假装相信便能同时容纳现实与非现实。沃尔顿在这个问题上引出的讨论是:“在体育赛事中,对于任何一位‘角色’应该承担的命运,其本身可能是没有答案的;这里没有现成的好人和坏人。”也就是说,体育比赛中不存在明面上的好结局和坏结局之分,而只在于支持者们认为哪一方获胜的结局要更好,不同的倾向便是在比赛进行时表现出不同的虚构情感。
当脱离此类游戏时,比赛中的队员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能在游戏之外的地方对这些对象产生真实的情感。因此,尽管我们将比赛视作特殊的虚构,比赛中的队员也不能仅仅被看作一种“虚构真实”,即不能将他们看作仅仅在游戏中是真实的。然而,在信念问题上,体育比赛和虚构作品不能一概而论。根据沃尔顿的观点,假设存在一个虚构作品或虚构故事f,参与者或观众相信f是完全虚构的,同时假装相信f为真。但是对于一场比赛,参与者会相信比赛是真实发生的,因为队员们都真实存在,如果将比赛看作一场假装游戏,那么参与者会在其中假装相信着什么?这是沃尔顿的假装理论需要解释的问题。
倘若按照沃尔顿的观点,恐怕观众是在假装相信这是一场“好人战胜坏人”的游戏,而事实上,“好人”和“坏人”并非现实存在,尽管我们能灵活地变换对好人和坏人的界定:假设有一场比赛f*,参与者或观众相信f*是部分虚构的,同时假装相信f*全部为真。但无论如何,我们对于f*的态度只会是“这只是场游戏”,正如我们对f的态度是“这只是个故事”一样。另一方面,从比赛本身来看,声称f*部分虚构意味着,体育比赛是现实存在的,其中的队员都是真实的,但这样的比赛依靠的是约定好的游戏规则,没有游戏规则就无法进行下去;而声称f*全部为真意味着,对于f*所使用的规则进行“暂时搁置怀疑”,而之后需要假装相信这种规则在游戏之外也起作用,这就好像在欣赏虚构作品时,假装相信主人公在故事之外仍然存在一样。
但是,沃尔顿没有深入论证的是,这本质上是一场没有必要的游戏。无论是查尔斯模型还是木桩与熊,本质上都存在一种规范,即让人以特定的方式进行想象,从而参与进游戏之中。而在比赛的情况下,并没有事先的规则规定我们一定要作“将队员当作好人或坏人”这般的想象。这恰好会与沃尔顿的理论冲突,因为他将不被授权和不加规范的想象看作破坏游戏的因素。沃尔顿倘若要将假装相信运用到比赛之中,那么他还要论证为什么这种规则是必要的,但显然,他在这方面的叙述并不充足,而这也是沃尔顿将假装理论进行延伸的困难所在。
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却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观众和读者是这些游戏当中的“自反性道具”(reflexive props),这生成了关于他们自己的虚构真实。
在先前的论述中,我们难免忽视的地方在于:游戏的参与者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使参与者沉浸于游戏中而进行“假装相信”,似乎意味着对参与者本身也要进行某种程度的虚构。例如,在桌面游戏《龙与地下城》(Dungeons & Dragons)中,我们会创造出某种有别于现实人物的角色,让这个虚构角色代我们进行故事中的冒险。这使得我们对虚构本身的关注转移到了参与者之上,参与者似乎需要在进行游戏时让渡一部分真实,如此才能参与甚至沉浸于游戏当中。
我说到,“化身”一词通常是指用于玩家识别的道具,但考虑到道具理论,这个说法可能是对其的误解。如果我们要以沃尔顿的方法来使用这个术语,那么“化身”必须指游戏玩家与相关虚构世界交互的手段……如果我们假设化身是一种道具(按照这里简述的沃尔顿的思路),它规定了玩家想象他们身处游戏的虚构世界当中……
在现代的电子游戏当中,“化身”屡见不鲜,甚至更为直观。例如,在著名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反恐精英》(Counter-Strike)之中,玩家们在游戏中的化身是“反恐人员”或者“恐怖分子”,并将彼此的斗争作为游戏继续进行下去。在各类角色扮演类游戏中,玩家在游戏中的化身是自定义的虚拟角色,并借助这一虚拟角色经历虚构的冒险。
沃尔顿本人在相关的论文和著作中没有讨论当今的电子游戏,但他注意到了体育比赛中蕴含的可能性,即体育比赛中存在将假装理论延续至其他媒介的可能,但这或多或少会给自身的理论带来挑战。在此处,沃尔顿首次表明了将假装理论进行跨媒介推广的倾向,体育比赛就是他尝试跨越传统艺术媒介的第一步。不过,对于新兴的电子游戏,我们只能从贝特曼记述的来信中窥得沃尔顿对于游戏的积极立场,甚至假装相信所涵盖的范围要更加广泛:
艺术是什么,或者如何去定义“艺术”,这是一个极其混乱的问题,而我认为这个问题没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重要……但是可能有很多人不会认为被看作艺术的东西也会涉及假装相信。我和其他人认为,假装相信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无处不在(隐喻、讽刺、语录、科学理论、宗教信仰、运动和游戏等)。
有了“化身”的引入,便能进一步解释我们为什么将体育赛事看作一场假装游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在比赛之中,即便我们对真实的队员是否能产生虚构情感持有疑问,我们仍然能对“化身”所处的虚构世界产生虚构情感。这或许是虚构世界为什么能令人信以为真的一个重要缘由,除了虚构作品生成的虚构真实之外,我们还想象自己的“化身”参与虚构世界,把自身当成玩家,把虚构世界当成一场假装游戏。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虚构世界涉及的信念问题,以及介绍了沃尔顿在虚构问题上的立场。这些讨论以拉德福德的“虚构悖论”为起点,试图以假装相信的途径来对“虚构悖论”进行更融洽的解释。沃尔顿的反实在论观点认为,我们对于虚构世界的情感实际上都不是完全真实的,而是在其中采取了假装相信的态度。如此,当我们脱离虚构世界之后,这种虚构的情感也会随着这样的态度消散而消失。
沃尔顿注意到了该理论的潜在可能,并尝试将体育比赛看成一场假装游戏来作为其理论的补充。但是,由于沃尔顿的出发点是儿童游戏,这一理论遇到的难题显而易见——要如何将这一理论从儿童游戏推广到其他的广义游戏。实际上,沃尔顿所做的可能只是将理论推广到了艺术作品(特别是电影、绘画和小说这种再现艺术作品)。在上述讨论中,要解释现代电子游戏当中的一些虚构和信念等相关问题,仅仅凭借沃尔顿的反实在论立场是较为困难的,尽管沃尔顿对此持积极的态度。
此外,随着电子游戏和网络的发展,每个人的“化身”都处在同一个虚构世界,而不是分处于不同的假装游戏世界中。玩家借助“化身”而身处同一个虚构世界,此时便遇到了体育比赛例子之中存在的问题:这只是一场游戏,但我们除了会产生虚构情感外,同时还会对“化身”背后的人产生真实情感。回到一开始的话题,存在的另一种回应是:虚构世界之所以能令人信以为真,还在于我们能在虚构世界中寻找到虚构真实之外的真实。事实上,沃尔顿的温和态度并非要表明准情感和真实毫不相关,但基于反实在论的立场,沃尔顿不去反对虚构对象实在而只是不承诺实在,已是其作出的最大让步。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需执着于某一方,更何况,如今的虚构世界已经不再是单纯封闭式的,而是已经在电子游戏中成为开放式的了。就像沃尔顿为贝特曼著作写下的推荐语那般——“对于许多种类的游戏而言,特别是数字游戏,这种审视是令人耳目一新且富有新意的”。面对现代的虚构世界,我们仍有许多可探讨且值得探讨的地方。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莫斌 常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