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工智能艺术是艺术语言的自动化生产和形式化尝试。首先,从语言角度解析图灵测试可知,图灵实际上是将思考等价于语言的自动生成,人工智能语言的技术逻辑是拟合与转码,而人工智能文本作为艺术被接受的关键在于人们的接受惯性与艺术共识;其次,人工智能艺术美介于自然美与艺术美之间,蕴含“有目的的不合目的性”,语言的自动化生产导致了衍文本的泛滥,人工智能艺术语言是一种物化的语言,人工智能艺术的形式化表明人们试图用技术为艺术寻找规律、为艺术祛魅,但是其内在化又促成了技术的施魅;最后,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形式化导致其辩证性的消失,这种艺术语言成了资本驱动下的智能文化产品,考察人机关系是为了避免人与机器的控制悖论,只有将人工智能视作行动者网络的一部分,成为平等对话的一方,人工智能艺术才能得到救赎。
关键词: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物化;辩证法;行动者网络
作者陶锋,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天津300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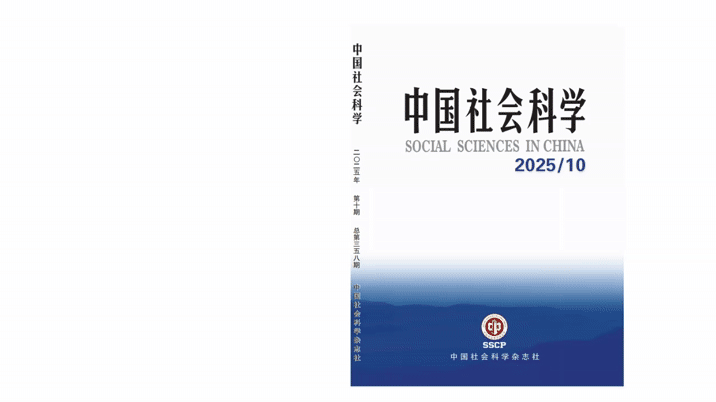
最近,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AI)的技术进展,表明人工智能在“智能化”水平上有所提升,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对传统的哲学和艺术难题的新思考,如主体性、意向性、创造性、艺术本质等问题,可以从人工智能艺术语言这一角度来切入,剖析并反思这些问题。
既然艺术与语言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那么,从艺术语言的角度来解析人工智能艺术的实质,分析人工智能艺术语言与人类艺术语言的联系与区别,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途径。艺术语言符号说是人工智能艺术的支持性理论和技术基础,而艺术广义语言说则是对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一种批判。从艺术的文化本质来批判人工智能艺术更为恰当:艺术语言不能只是元素的组合和堆砌,社会维度和现实关系是其更重要的本质。
“人工智能艺术”是一个新兴的却又含义模糊的范畴。狭义地理解,人工智能艺术指的是人工智能在接到简单指令后自动生成艺术作品。从人工智能的功能和地位来看,人工智能在该类艺术中可以被视作具有一定主动性的“代理”。在这种自动生成系统中,人工智能并非像“计算机艺术”中的计算机那样,只是一种生成工具或者媒介,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艺术生成中能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从版权的角度来看,为人工智能输入简单指令的人并不拥有该艺术的版权,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人在该类艺术生成中不是主导者。
广义的人工智能艺术还包括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合作生成的艺术,如人机交互艺术。在这类艺术中,艺术家仍然是艺术品的构思者和主导者,人工智能生成是艺术家整个艺术装置中的一部分。笔者所批评的人工智能艺术语言,主要是针对人工智能自动生成艺术这一部分。
人工智能艺术(特别是自动生成艺术)打破了传统的人类艺术概念,引发了人们对传统艺术概念的反思:是不是只有人造的艺术才能称作艺术?我们应该如何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和人创作的艺术?人工智能生成艺术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拥有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机器是否最终将取代人类艺术家,人类艺术是否将终结?之所以有这些难题,是因为我们仅仅从艺术品这一表象来看待人工智能生成艺术,而忽视了表象背后的生成本质和语言特征。艺术品是艺术活动的结果而非全部,而且这个结果往往会被附加上接受者的文化和情感因素。然而艺术并不等于艺术品,不能倒果为因。当我们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包括语言的特征、生产机制和交往过程)去整体理解人工智能艺术时,我们才能深入解析其蕴含的本质属性。
一、图灵测试之误:人工智能艺术语言问题的引出
(一)规则与功能:维特根斯坦与图灵之争
人工智能专家普遍认为,所谓的智能、心灵、想象力、情感等概念,是一些内在的、难以被实证的预设,必须通过外在的行为(包括言说)及其产物(如艺术、语言等)才能被表征或体现出来。图灵指出,只有通过某种行为测试(即语言问答),才能去理解智能(思考)。因此,他将“机器能思考”的问题等价为“机器能通过语言测试”。这种等价会产生几个疑问:(1)“使用”语言等价于思考吗?(2)用语言回答问题等于能够“使用”语言吗?(3)语言(问答)可否自动化生成?自动化生成的语言与现实是何关系?(4)语言(问答)的自动化生成等价于思考或者智能吗?图灵的这种行为功能主义立场遭到了许多哲学家包括维特根斯坦、塞尔等人的猛烈批判。历来批评图灵的观点都集中在了前两点上,笔者则认为实际上后两点才是图灵测试错误的根本所在。
早在图灵测试被提出之前,图灵和维特根斯坦已经就“机器能思考”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思想上的交锋。维特根斯坦从语言游戏的立场出发,认为抛弃语言规则和前提去随意使用一些概念,会导致语言的误用。“思考”“感知”“愿望”这类词语,表明其行为主体只能是人或者其他有智能的生命,而不适用于非生命体。然而,自从图灵作出“机器能思考”等价于“机器能模拟思考的行为”这种预设后,人们将“思考”这个词语不断地用于机器、人工智能等非生命体。仅仅从语法规范的角度来消解机器思考问题已经不再现实,语言本身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语言规范也会不断被打破和重建。
图灵测试正是一种基于行为的功能主义的测试,图灵混淆了智能与思维以及思维活动与思维结果。他将思维等价于语言的问答,认为机器只要像人一样回答问题,就有了智能。然而实际上,虽然现在的大语言模型(如ChatGPT,DeepSeek)已经能通过图灵测试,大众难以辨别真假,但这并不意味着机器有了智能和思维。这种语言的问答只是一种数据上的拟合,是对“语言”进行模仿的游戏。语言的模仿游戏不同于思维活动,更不能反推出思维,而是一种语言符号的生成、重组和配对,可以视作一种“语言”的自动化生成和生产。图灵测试混淆了思维与智能,将语言问答简化为语言的生产,这使得复杂的智能问题能够用一种问答行为测试的方法进行判断。所以人工智能专家纷纷以通过图灵测试作为其研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这导致了一种机器智能研究的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
(二)拟合与转码: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技术逻辑
图灵测试的基础和媒介在于语言,当我们深入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时,就可以找到回答技巧的本质是什么。由于自然语言具有复杂性、歧义性和可变性,所以人工智能语言的基础算法是通过概率算法(如隐马尔可夫模型)来预测语词搭配、语义等,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语句的生成。换言之,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只能做到与自然语言在形式和功能上的近似或者说拟合。无论是大语言模型还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都并不是真正地在回答问题,更谈不上思考。语言的自动生成显然不等于机器能够言说,更不代表机器能够遵守语言规则乃至具备思维能力了。
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生成语言,同样,它也能够自动生成艺术语言(符号),包括文学性语言、视觉符号语言、听觉符号语言等。不少视觉图像算法的基础其实是语言处理,这涉及语言与图像的关系与转换,即文生图(text-to-image)技术,如应用了clip模型的Dalle-2、Stable diffusion。深入研究其生成机制会发现,我们之所以可以通过输入提示词(prompt)来生成图画,其深层逻辑是将图画和语言符码化,转换成人工智能可以处理的高维向量(数值特征),然后通过语义对齐技术,将文本向量与图画向量对齐(在向量的空间位置接近或者一致)。这种转码技术说明,人工智能根本没有理解文字命令,仅仅只是通过数值上的拟合,实现图片的生成。现在的文生视频技术也是如此。
(三)接受惯性与文化幻象:人工智能语言的艺术化可能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在阅读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时仍能感受到情感或者文化呢?这是由于人们长期阅读之后形成的一种接受惯性,以及读者与词语之间达成了艺术共识。接受理论认为,读者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如果没有受众的积极参与,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只有通过它的中介过程,作品才会进入一个不断变化的体验视野”。对于读者而言,这种主动参与当然是一种积极的阅读活动。但是它也会产生一种接受惯性,即读者会通过联想、完形机制来补全、强化作品。这使得空洞的人工智能作品被读者强行赋予了原本没有的情感和文化内涵,从而形成了情感和文化幻象。人工智能技术正是借助了这种惯性,通过“感情计算”等方式来制造幻象,生成所谓的“艺术”。
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领域的广泛应用,说明艺术不仅可以被技术祛魅,同时技术本身也可能被施魅。人类艺术被还原为数据、数字和数学,技术也正在成为人们新的膜拜对象。一些技术研发者刻意制造噱头甚至焦虑感,在他们的渲染下,似乎通过了图灵测试,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具备创造力和想象力了,甚至可以替代艺术家了。因此,对人工智能艺术生成的解魅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从哲学上来考察,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生成的本质是什么呢?其有何内在动力呢?它们和人类的艺术语言生成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二、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本质阐释
当我们从技术层面理解了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生成机制,才能进一步明白其审美的独特性,弄清楚其语言与人类艺术语言的本质差异,从而不会轻易地将创造性、想象力、文化等人类特质赋予人工智能。
(一) 自然美、艺术美与人工智能艺术美
人工智能作品是人类艺术形式的重新组合和再造,因此它可以引发一种形式审美。但是这种美感又和人们欣赏自然、人类艺术时稍有不同,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美感,而是掺杂着其他内容的感受。
康德区分了自然美和艺术美,他认为自然美是“一个美的事物”,而艺术美则是“对一个事物的美的表现”。他还指出,艺术与其他生物活动不同,“人们仅仅应该将那种通过自由的生产,也就是通过以理性为其行动的基础的任意性的生产,称为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并非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自由生产活动,这种生成中缺乏人类的创作和想象活动,因此很难被视作一种人类艺术。人工智能作品(特别是艺术产品)也不能简单地被视作人工制品,很多人工智能作品是在程序下自动生成的,超出了人类设计者的预想。人工智能作品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形式美——人工智能艺术美,它能够为人所感知和欣赏,但是它既非自然美,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美。
“X的美”(beauty of X)的命题是从人的审美判断的角度讨论,这种判断更重视的是事物(X)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一种主观层面的形式判断。美丑判断被现代哲学家视作一种主客对立思维下的判断形式,阿多诺、海德格尔等人提出了超越主客二分的美的显现方法。阿多诺认为,应该用“艺术语言”去取代所谓的“美”,所谓的“X的美”应该是“X在言说”,人去倾听和理解这种言说,而不是将自己的主观美丑标准强加在X之上。所谓的“美”应该被艺术语言的“真理内涵”所取代。阿多诺在这里进行了一种从审美价值到本体论价值的转换。只有人的审美判断真正符合客体言说的真实,才是美的。阿多诺认为,自然美是自然无声的语言,而艺术美则是对这种自然语言(自然美)的模仿(imitation)和翻译。
由此,整个艺术品和文本的人类属性可能会发生彻底的改变。未来我们看到的翻译文本甚至艺术文本,绝大部分都是经过人工智能处理甚至是其生产的。如果任其发展,人类的作品会被机器不断自我复制的艺术符号所湮没。
综上,人工智能艺术并不是传统的人类艺术。它打破了艺术必须由人创造、必须以理性为基础的界定,从而扩展了艺术的概念。人工智能艺术所体现的美也不同于自然美和艺术美,它有艺术形式因素,这些因素能引发人的审美感受,但是它又不是来源于生活、对应于实在的。人工智能艺术是一种语言形式的自动化生产,而非人类有意识的语言。
(二)衍文本与物化语言:文本自动化与无根性
人工智能作品是一种衍生的人工物,从艺术语言理论来说,我们也可以用“衍文本” (derived text)来概述这种自动化生成艺术语言,“衍”有衍生和繁衍之意,衍文本意味着人工智能文本是从人类文本衍生而来,但是由于其自动生成功能,类似于语言的自我繁衍。衍文本与“衍文”和“超文本”相关,但由于其具有AI技术的属性而生发出新的含义。
“衍文”的原意是指因缮写、刻版、排版等错误而多出来的字或句子,即因技术错误导致的文本讹误。衍文本则是有意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去生成文本,这种文本的功能和目的是恰当的,然而当它不断自我复制时,文本与其最初的语境和现实环境越离越远,会导致文本的无意义和错误。衍文本和超文本有一定的相似性。超文本指的是通过使用文本链接,使空间的文本(后来扩展到不同媒介的文本)在网络上实现链接和交叉引用。超文本概念的提出者尼尔森认为更广义的超文本指的是一种非连续性的写作。与超文本的相似之处在于,衍文本也主要在网络上分享,也是一种打破传统时间性的文本。
在网络时代之前,语言(包括文本)的自我衍生早已开始。海德格尔、巴特、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曾经设想过,语言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立性。海德格尔认为,人并非语言的塑造者和主宰,相反,“语言是人的主人”。语言是存在的规定性(语言是存在之家),艺术(诗歌)是本真的语言。人工智能可以源源不断地、自动地生产(艺术)语言,由此看衍文本似乎蕴含了独立性。然而,这种语言只是一种纯粹符号化的、内在化的语言,它在独立的那一刻就注定已经死亡了。海德格尔不可能同意一种纯粹符号化的、内在化的语言存在,他认为,符号、指令等构成的技术语言是对本真语言的攻击,人工智能艺术语言也不可能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之家”。
巴特设想过一种理想的(阐述)文本,这是一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的文本系统,这种文本没有开端,没有主线,是不确定的,是基于语言的无限性的。巴特虽然不可能设想一种网络上的超文本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衍文本,但是他的理想文本却成了超文本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超文本具有非线性、去中心化的特征,这一点和人工智能衍文本是相似的。当人类文本输入人工智能等程序中,经过重组、改造、重新构型,文本的源头变得难以追溯。相较于超文本的转链接能力,衍文本的特点在于基于强大计算能力的文本无限繁殖性。这些不断生产繁殖的文本可以重新流入人类文本池,甚至再次作为原始数据输入程序中,这种情况又被称作“产业自循环”。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这种自循环会让机器生产的数据缺乏多样性、偏离真实世界,最终导致“模型崩溃”。这种崩溃可能仅仅是开始,如果未来人类世界的语言和文化建立在无数的机器生产的文本上,那么人类文明大厦也有随时崩塌的危险。
当衍文本繁殖得足够多之后,人工智能学习的就不再是人类的文本,其生成的文本就成了无根之物了。无根性意味着衍文本与其现实来源发生彻底断裂,人工智能正在生成一个逐渐闭合的符号世界。这种封闭性是符号、语言、艺术等人类文化形式的内在化、理念化的极端体现。最初,莱布尼茨、弗雷格等思想家孜孜不倦地追求一种人工形式语言,促使计算机与人工智能技术语言的诞生。如今这些技术又反过来促进了形式化语言的自动化生产。技术化语言最终切断了语言与人类以及现实的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无根的、漫游的符号。这种符号要么是机器生产出的商品(具有交换性),要么是无价值的废品,一直源源不断地衍生出来。体现在人工智能艺术中,少数作品成为文化工业产品,进入艺术市场中,更多的生成物则变成了电子垃圾。
(三)形式化与内在化:人工智能艺术的祛魅与施魅
人工智能艺术的基础是数学,用数学来实现艺术的形式化和算法化也是许多美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目标。早在古希腊时期,对艺术和美的形式化追求就已经开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的和谐就是美,黄金分割率即是一种例证。然而中世纪宗教又为艺术神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则为艺术规律化、形式化提供了可能,同时也在破除艺术的神秘性,艺术始终在施魅和解魅中纠缠。格式塔心理学结合了现代物理学中的重要概念——“力”,发展出了“知觉力”的概念。阿恩海姆认为,客观事物的物理结构和主观的知觉力是相互作用的,艺术中的一些平衡、形状、色彩、运动可以引发人类的视知觉力量,从而传递表现性。只要能够找到蕴含表现性的式样和力,就能引发审美感受。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为艺术的形式化提供了合理化基础。
真正试图将计算引入艺术和审美中的是信息美学,该派学者认为,审美和艺术品中传递信息,这种信息可以量化,他们试图为艺术形式、审美理念总结出信息公式,如伯克霍夫提出的审美信息量度(M)与秩序(O)和复杂度(C)直接相关。这为人工智能艺术生成和评价提供了一种可能,用信息美学的计算公式来看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学作品(笔者曾用ChatGPT生成长篇剧本),就会发现其复杂度较低,信息量不足。实验美学则认为审美形式可以引发人类不同的审美心理,主张用实验法去总结出美的规律。新实验美学倡导者贝里尼提出了唤醒理论(Arousal theory),该理论认为艺术形式与唤醒潜力之间有着相关性,因此,艺术家应该通过技巧来调整作品的秩序和唤醒元素。这种量化分析已经被专家运用于人工智能艺术中。
人工智能艺术为艺术语言形式化、内在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人工智能艺术生成一般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自上而下的符号主义方法,此方法预先设置好艺术生成程序,包括图形、色彩、构图等,如Aaron绘画程序等。这种方法需要运用已有的艺术形式规律和理论,因此存在着理论滞后性和片面性。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联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运用了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深度学习,通过输入大量的人类艺术样本,让人工智能程序“学会”如何生成相似的艺术文本。最新的Difussion 算法则进一步通过解码与还原解码,以及文本—图像转换技术,让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具有了很高的真实性以及创新效果。
艺术的形式化是人们为了祛除艺术神秘性、寻求艺术规律性的结果。而形式化也可能会导致艺术的内在化,即发展成一种自洽的艺术形式系统。这种艺术形式系统如果过于封闭,必然会导致其与外在世界慢慢脱离,而形成一种自足但抽象的符号系统。人工智能艺术的内在性形成一种新的神秘性——技术的神秘性,普通欣赏者一般不需要也很难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生成艺术的过程,人们看到的只是技术可以魔法般生成大量作品,技术用艺术来炫耀自己的能力。本雅明所说的艺术“震惊”感转变为了对“技术生成”和技术本身的震惊体验。人们通过技术,一方面给艺术祛魅,另一方面却形成了新的技术之魅。
然而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并不能像数学那样高度形式化和内在化。首先,数学可以内在化,其基础是数理逻辑和数学推理。而艺术品的形式虽然可以进行一定的内在化,但是其内在规范并非因果推理和形式逻辑的(有人称之为“想象的逻辑”,而是具有辩证性的。其次,数学并不需要实在化,而艺术必须形成作品、必须“物质化”(materialization)。在这个物质化的过程中,由于环境、工具、媒介等变量的影响,艺术品会具有人类无法控制的偶然性。最后,数学公式的成立并不需要外在世界的验证,数学不受外在标准和价值观影响,其标准为逻辑上的真假。而艺术必须呈现给观众,外在标准和价值观对其有决定性影响,美丑等标准是由观众所判定的。
综上,形式化是人工智能艺术生成的基础,部分艺术要素确实可以形式化、抽象化。然而,艺术又是具有创新性和否定性的,艺术家不断地打破已有的规律,创造出新的艺术范式。艺术的真理性不仅仅在于艺术形式要素的配比,还在于艺术与实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符合关系,而是一种融合的关系。因此,脱离了实在的、完全内在化的艺术只能是一种艺术语言游戏,而非本真的艺术。
三、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批评与引导
人工智能艺术语言是形式化和内在化的符号式语言,这种艺术语言和本真的艺术语言的本质区别何在?它背后的驱动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们又如何去改造这种艺术语言形态,使之成为人类艺术的有益补充呢?
(一)辩证性的丧失: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空洞化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绝大部分思想家都认为艺术具有辩证因素。阿多诺进一步认为,艺术作为语言,具有表达不可表达之物的辩证性。这种辩证性恰恰是人工智能艺术语言所缺乏的。
首先,艺术语言的辩证性体现在其试图表达不可表达之物。阿多诺认为,哲学和音乐一样,都具有一种悬浮性,而这是很难付诸文字的。“本真作品也是一种绝技,即实现那些不可实现的绝技”,艺术的“绝技”就是这种“悬浮”(表达不可表达之物)的感性例子。艺术的根本目的是将事物语言真实地表达(翻译)出来,而不是一种脱离现实事物的语言游戏。而这恰恰是人工智能艺术语言所无法实现的。
其次,艺术虽有其逻辑,然而这是一种悖论式逻辑。“音乐的‘游戏’是一种具有逻辑形式的游戏:陈述、同一、相似、矛盾、整体和部分的形式”,音乐的逻辑虽然与真理有关,却并非“判断逻辑真理”(apophantic truth),而是“逻辑的无判断的综合”。艺术虽然是一种语言,但却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语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程序(算法),需遵循数理逻辑,是不能允许悖论存在的。基于深度学习的AI艺术算法可以对人类艺术语言进行统计性归纳,某种程度上倒是可以模拟一种悖论式艺术语言的表象,不过这种建立在统计规则上的模拟缺乏悖论的张力,只会导致艺术语言的平庸。
最后,艺术的辩证性还体现为作品建构的悖论性。阿多诺指出,“建构”一词来源于技术,指的是“许多给定元素的合理化标准”,艺术不是“为这种真正的实用目的服务的”。艺术根据建构原则将会导致一种“审美严格性”,艺术作品成了“数学练习”,这与艺术原则背道而驰。艺术具有辩证性意味着艺术永远无法像科学那样去追寻必然性,它一定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性和否定性是艺术对社会批判的基础,是艺术需要永远保留的特质。这就意味着,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的人工智能艺术只能是一种艺术语言的形式游戏,不应该成为艺术的核心部分。
当我们将艺术设置为一种艺术语言的自动生产时,艺术趋向于空洞。它的内在结构从辩证的、复杂的变成了确定的、单维的,其外在价值如批判性、否定性以及救赎性完全丧失,艺术与人的关联也将丧失,艺术蜕变为漂浮在人类世界中的无根符号。重提艺术的辩证法并非为艺术的神秘性招魂,而是希望重视同一性结构规训下的非同一之物,技术在为艺术解魅时,不应该将自身树立为新的偶像,技术崇拜会导致新的技术同一性和技术非理性。
(二)资本驱动与智能文化工业:人工智能艺术语言的生产
人工智能艺术语言本质上是艺术符号的自我复制和增殖,这不仅仅是AI技术的计算本质造成的,还因为它的根本驱动力是资本。在社会的商品生产阶段,物品是作为商品而生产的。艺术语言也可以是一种商品,人工智能艺术语言因其可复制性,是一种理想的工业化商品形态。
当然,智能文化工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大众的生活、提升了艺术工业的生产效率。我们应该警惕那种具有控制性、同一化的资本体系通过技术对人进行控制和异化。艺术本来是对资本控制性和同一化思维的反抗,如果任由资本和技术来控制全部艺术,那么人类世界中的非同一性部分也将逐渐消失。艺术语言应该是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媒介。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他人分享情感。但是当艺术语言成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形式符号时,特别是这些海量的符号将人类与世界、与他人逐渐隔绝开来之后,人们就难以真实地感受到世界和情感的实在性了。
(三) 人机关系与行动网络:人工智能艺术的引导
正因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逐渐隔绝开来,人与机器的关系反而日益凸显,人机关系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人机互动以及人机信任上。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强人工智能——有意识的人工智能。而现在的人工智能水平虽然还实现不了意识,但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模拟智能或心灵的功能与表征。图灵测试实质上在鼓励机器以一种伪装为人的方式与人交流,技术专家忽视了这种技术带来的信任问题。维特根斯坦论证过人类“装假”的问题。他认为“装假”像一种游戏,出现在他人内心。人们无法确定他人的内部,但是内部事项也必须在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人无法从外部来确证机器是否有“心灵”,就如同人无法知道他心一样。因此,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人机互动考察的重点并非人与机器的心灵交流问题,而是人与机器在实践和生活上的关系,以及两者的行动选择和责任问题。
结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马涛 责任编审:张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