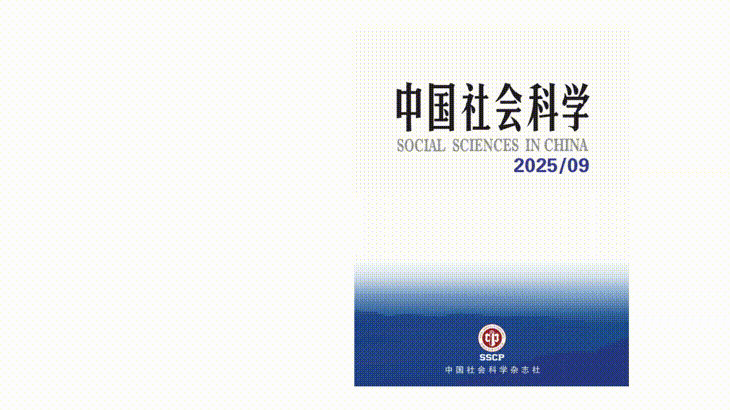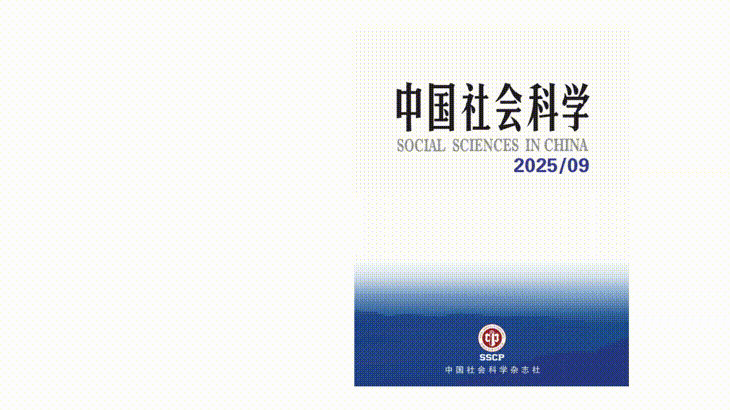
中国幅员辽阔,在这个广袤的范围内有不同的地理单元。因环境不同,在各地理单元内产生、发展出不同的区域文化。早在万年以前,因为环境和气候的差异,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就分别产生了粟作和稻作农业,农业带来人群的定居和文化的发展,“北粟南稻”的农业格局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此后,各区域的文化形成鲜明的特色,社会出现分化,文明元素在各地萌生。大约从距今6000年开始,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火花。各区域的文化彼此互动交流,逐渐形成“早期中华文化圈”。从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开始出现。大约3750年前,在中原的核心地区出现了二里头文化。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出现了体现“择中立宫”规划理念的大型都邑,出土了成组的青铜容器和玉器。二里头文化代表着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二里头文化的礼仪制度和文化思想广泛影响到其他地区,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华文明从此进入中原文化引领的新阶段。二里头文化也因此被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在从二里头至秦汉时期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原以外的区域文化不断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宏大且多条线索交织的进程,不同区域的进程各不相同。只有对所有区域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才能丰富文明发展进程的细节和多元一体格局的内涵,并形成相关的理论认识。本文将从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来认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选择西南地区进行考察,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西南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从公元前2千纪到秦汉时期,在整个中国青铜时代,西南地区的青铜器具有某些突出共性,这使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在整体上构成一个明显的文化单元。第二,西南是距中原较远的区域,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也最为复杂多样、异彩纷呈,正是在青铜时代,西南各区域的文化发展到高峰,随后开始一体化。因而,考察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历史走向,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认识。本文以西南地区青铜文化为依据阐述文化多样性生成的原因,并力图找到实现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一、中国青铜时代的西南
考察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首先需要认识这些青铜文化存在的时空背景,选择研究的切入点。
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铜器遗存,其年代可早至公元前5千纪开始的仰韶文化时期,这包括非常零星的黄铜、红铜、青铜器残片及炼渣等。直至公元前18世纪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器才开始大量出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有容器、兵器、工具、铜铃、牌饰等。在二里头宫殿区以南的围垣区发现面积约1.5万—2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出土大量铸铜遗存。根据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特别是考虑到二里头铸铜手工业的规模、技术和此后成为青铜礼器核心的青铜容器,以及二里头青铜器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我们认为二里头文化开启了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商代后,中国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高峰。中原地区的商文化以高超的技术创造出大量绚丽的青铜器,在商文化的影响下,中原以外的广阔区域,包括长江流域的很多地区都进入了青铜时代,发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中国的青铜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又形成一个高峰,到了秦汉时期,在很多地区青铜器的重要性开始显著降低。与青铜器的衰落相关联的是铁器的出现与普及。现有的考古材料表明,在公元前800年前后黄河流域就出现了人工冶铁,至公元前3世纪时,铁器已在全国很多地区普及。铁器、漆器等新兴器物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青铜器。但全国各区域的文化、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仅就西南地区而言,四川盆地在相当于商代晚期时出现了发达的青铜文化,但在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才发展到高峰。因此,要全面理解中国的青铜时代,需要对近2000年的时段进行整体把握,对于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也要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认识。
理解中国的青铜时代及各地的青铜文化,青铜器是关键。青铜器集中体现了青铜时代的技术和文化成就,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因而最能代表文明的发展水平。在中国,除兵器和工具等实用器具外,青铜器更被作为礼仪和祭祀用具。青铜器集合了贵重资源与复杂技术,成为拥有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占有青铜器的人掌握了沟通天地的手段和统治社会的权力。尽管如此,不同地区的青铜器的具体内涵、功能,以及对社会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尽相同,这一点又导致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在整体中包容着差异。
笔者曾依据青铜器,将中国的青铜文化分为四大区域。第一个区域是中原,最重要的青铜器是礼器;第二个区域为长城沿线的北方地区,青铜器主要是实用的兵器和工具;第三个区域为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最有特色的青铜器为铙、钟、鼓、磬等乐器;第四个区域即为西南地区,最具特色的青铜器是象征性、写实性、表现场景的器物,这类青铜器集中发现于四川和云南。结合近年的考古新发现,我们可以将这一认识进一步向前推进。
中原青铜礼器的铸造技术、器类、功能,都以二里头文化为开端。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商代,青铜器的生产主要由王朝控制,以青铜器为核心的贵重物的生产和流通,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经济主干,支持了社会等级制的形成和运行。青铜器形成固定组合,铸刻铭文,主要用于典礼、祭祀、丧葬等。公元前5世纪之后,青铜器开始逐渐转变为生活实用器而不再用于支持等级制,但中原青铜器蕴含的观念对其他区域和后世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城沿线的北方地区主要是从内蒙古东南部到甘肃一带,地貌多为山地、草原、沙漠、高原。这里历来就是一条地理、经济形态和文化的分界线。在燕山以北,大约公元前2000—前1400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铜斧、杖首、耳环、指环等。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遗址,出土了最早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兵器、工具、容器和装饰品。此后兵器、工具、生活用器、装饰品、车马器等大量出现。北方地区的青铜器也用于宗教或祭祀活动,但更多是实用器,铜器的生产、使用与游牧生活相适应,同时也受中原和欧亚草原地区其他文化的影响。广阔的区域、流动的人群、活跃的文化交流,使北方地区的青铜器更多具有实用性,人们难以把特定的观念赋予到铜器中,并将铜器的使用规范化和程式化。
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区,最早的青铜器可能出现在商代中期。南方地区除出土与中原相同的器类外,还有丰富的乐器,这一特点非常鲜明。在江西新干一座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大墓中,出土了3件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青铜铙。更多的各种类型的铜铙出自湘江流域、赣江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至迟在西周早期,出现了铜钟,钟在南方的分布范围基本与铙相同。南方地区还有商周时期的铜镈、鼓、磬,尽管数量不多,但这类乐器不见于其他区域。南方的乐器多零散出土,绝大多数不用于随葬。
西南地区最早的成批青铜器出自四川广汉三星堆的8个祭祀器物坑。这批铜器的主体是象征特定对象或表现祭祀活动场景的器物。前一类包括青铜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鸟等,后一类有神坛,顶尊人像,执璋人像和各类站立、跪坐的人像等,这些铜器体现了太阳崇拜这一原始信仰。同类铜器也见于成都的金沙遗址。具有象征性和表现场景的铜器在西南地区还有大量发现。一个区域是四川盐源盆地,盐源从商周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其中就有铜车马模型、铜人,以及人形和动物形的杖首、枝形器等。另一个区域是云南,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的滇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上万件青铜器,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以写实的器形、立雕、纹饰来表现场景的器物,场景几乎涉及当时人们的各种主要活动:战争、生产、狩猎、祭祀、纳贡、结盟,等等。这些铜器虽然出自墓葬,数量多寡可以指示墓葬等级,但并没有固定组合,自由、写实的风格和对场景的生动描绘,使得这类铜器缺乏中原青铜礼器的含义。
以上四个区域的铜器是就其主体或突出特征而言,各区域之间并没有明确界限。相反,因为相互交流和影响,各区域的青铜器有很多共性。比如,中原的青铜礼器在各区域普遍存在;北方和西南地区,存在风格相近甚至相同的青铜兵器、工具、装饰品。而在一个大区域内,青铜器的面貌与风格也具有多样性,即使是本地生产的铜器也是如此。本文将要进一步讨论的西南地区的青铜器和青铜文化,就充满了复杂性。
整体考察西南的青铜文化,除着眼于上述青铜器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20世纪80年代,童恩正提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理论,认为在从我国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高地上,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铜器时代,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元素,其中就有风格相同的青铜器,如动物形纹饰、人形茎铜剑、曲茎铜剑、曲刃铜矛、铜罍等,此外还有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石头建筑,以及球形石器、穿孔石器、半月形石刀、石范、双耳陶罐、双联陶罐等。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形成,是因为这个地带内的生态环境相似,地貌、太阳辐射、气温、植物生长期、降水量、湿润度、植被与土壤等具有一致性;同时还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即不同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使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只能在这个从北到南的地带内活动、迁徙。这个理论如今得到大量考古新发现的验证、充实,围绕“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认识,更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潜能。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正经过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两个区域的青铜文化因而具有相似性。四川盆地不在半月形地带上,但考古资料表明,成都平原的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都深受这个传播带的影响,三星堆和金沙这样的重要遗址,就位于半月形地带的边缘。
二、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多元文化
西南可以被视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文化单元,但具体到其内部,情况却很复杂,我们至少可以将之分为四川盆地、川西高原、云贵高原三个区域,每个区域内又有若干文化区。
(一)四川盆地
四川盆地是西南地区最接近中原文化区的区域。在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大约为公元前13世纪至前8世纪的三星堆—金沙文化,是西南地区最发达、最重要的青铜文化,其中心在广汉三星堆,在那里发现了格局复杂的城址,城内有人工修筑的大型台地、建筑、作坊、器物坑等。次中心是成都金沙,它曾与三星堆城并存过,但延续时间更长。在金沙也有大型建筑、居址、墓地和作坊。两个遗址都有祭祀区,出土数以万计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海贝等。这些遗物分为三大类,即以青铜神树、金太阳神鸟为代表的象征性器物,以青铜神坛和人像为代表的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以青铜容器、象牙、海贝等为主的祭祀用器。这些类别和面貌独特的遗物,集中反映了三星堆—金沙文化最突出的特征,即太阳崇拜以及因这一信仰而形成的神权。考古材料显示,当时的社会已呈现出早期国家的形态。三星堆和金沙的考古发现还表明,成都平原汇聚了来自四方的包括资源、技术、观念在内的大量文化元素,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成都平原地处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地可能存在一个观测天象、沟通自然、获取神秘力量的神性中心。进入东周后,成都平原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三星堆和金沙的中心城邑、祭祀区都不复存在,大型墓地和墓葬大量出现,如成都青白江的双元村墓地、成都商业街船棺墓、新都马家墓等。东周时期的墓葬有土坑墓、船棺墓、木椁墓等。青铜器都是随葬品,有两类。第一类是四川当地的器物,有釜、甑、鍪等容器,戈、矛、钺、剑等兵器,斧、刀、凿等工具,印章等杂器。容器形制简单,大多没有纹饰,兵器和印章上多有“巴蜀符号”。第二类为具有域外风格的铜器,有鼎、甗、敦、豆、壶、簠、缶、罍、鉴、匜等,形制复杂,纹饰多样,有的甚为精美。这类铜器的器形、纹饰,所运用的镶嵌、线刻工艺和失蜡铸造法,甚至部分铜器本身,来源于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变革可能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三星堆—金沙时期的太阳崇拜信仰不复存在,统治社会的神权瓦解;二是长江中下游的人群大量迁入。上述墓地表明,东周时期成都平原上族群林立,各种世俗和军事势力并存。墓葬、青铜器组合虽存在明显等级差异,但未形成规范,由此可见当时的成都平原内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权。
东周时期的墓葬在盆地东部直至峡江地区都有发现,最重要的有宣汉罗家坝和涪陵小田溪墓地。这两处墓地所在的嘉陵江、渠江流域和乌江下游在东周时期是巴人的分布区。罗家坝墓地被认为是巴国賨人的遗存,墓地出土的铜器与成都平原东周墓随葬铜器相一致。罗家坝是联系中原、长江中游和成都平原的时间、空间上的重要节点,其墓葬文化代表了四川盆地东周时期文化变化的开端。小田溪墓地被认为是巴国先王陵墓所在地,其中出现了明显的秦文化元素。这些墓地不仅揭示出东周时期四川盆地东部的文化面貌、格局和社会样貌,而且有助于我们对四川地区青铜文化的演进形成更具整体性的认识。
总体而言,东周时四川盆地内的墓葬及出土遗物大体相同,青铜文化已基本一致,这一文化可统称为巴蜀文化。
(二)川西高原
川西高原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各种考古学文化分布广泛。这个区域的青铜时代大体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战国,但到东汉时仍存在大量青铜器。这个区域的地理环境复杂,自然条件差异大,农业、畜牧业、采集、狩猎等多种生业方式并存。考古材料表明,区域内族群多,人群流动性大。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这一区域内有夷系、氐系、羌系族群,但目前还难以将各地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具体族属相对应。以上都导致了区域内的文化复杂多样。但川西高原青铜时代的文化也有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石棺葬。石棺墓在岷江上游分布最集中,茂县、汶川、理县境内都有多个墓地,在青衣江上游甚至在青藏高原东部和金沙江中下游都有发现。各地石棺墓的形制、特点又有差异,但都用石棺,墓中多出土双耳陶器,青铜器主要有武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在这些石棺墓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是茂县牟托的1号石棺墓及3个器物坑,共出土遗物250件,青铜器有鼎、罍、盏、敦、钟、戈、剑、牌饰,另有铜铁合制器、玉石器、陶器、竹木器等。这是川西高原随葬品最丰富、规格最高的石棺墓,内含石棺葬文化、中原文化、巴蜀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集中体现了川西高原青铜时代复杂的文化面貌和活跃的区域交流。
从川西高原往南,川西南盐源盆地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呈现独特性。在盐源的老龙头墓地出土大量墓葬和大批青铜器。截至目前,已发现墓葬1800多座,年代推测最早可到商代晚期,延续至西汉,可能是笮人的遗存。大中型墓有木质葬具或石棺,墓口用巨石覆盖,少数墓内随葬马或在附近设马坑,小型墓普遍有棺痕。墓葬随葬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玻璃器、陶器、石器、骨器等。最具特色的青铜器有釜、鼓、钟、铃、俎、案、杖、树形器、车马模型、纺织工具,种类和数量最多的是戈、矛、刀、剑、钺、斧、凿,以及镯、带饰、泡饰、动物形饰片和马具。铁器主要是矛、剑。这些考古发现中,铜树形器等具有鲜明的当地特点,但也可见很多外来文化元素,比如遗物中的铜车马、带銎铜器、靴形铜钺、铜鼓、金器、玻璃器、玛瑙、海贝等,尽管数量不多,但有很强的指示性。树形器、杖、车马模型、带銎铜器、金器以及随葬马的习俗等,显示出与北方的交流;铜鼓、靴形钺等则与云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关,叠葬的习俗在云南也有发现。这些都表明盐源盆地对外交流广泛,文化明显具有多元性。但上述文化元素并不见于四川盆地,盐源盆地的青铜文化显然与川西高原的关系更为密切。盐源考古材料的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汉初年,在盐源还有生产铜器的迹象,这些都意味着这个地区的青铜文化存在了很长时间,而不只是单纯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留下的一时的遗存。
(三)云贵高原
云贵高原同样是一个广阔区域,青铜文化更为复杂多样,学者们曾进行过不同的区系划分,比如杨勇将云贵高原的土著青铜文化分为黔西北、黔西南、昭鲁盆地、滇池地区、滇东高原、滇西高原、滇西横断山区、滇东南八个区域。
从考古发现看,滇西北最早出现青铜器。在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了云贵高原年代最早的小件铜工具和石范,还有大规模的滨水木构干栏式建筑群,以及稻、粟、麦等指示区域交流的农作物遗存。海门口是滇西北的一个重要聚落,青铜时代遗存的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距今3800—2500年。在海门口还有二次捡骨分层丛葬的葬俗。在剑川鳌凤山发现战国至西汉的墓葬,出土铜器、陶器、玉石器等。滇西北也是石棺墓和大石墓的分布区。滇西北应是云贵高原最早接触北方文化元素的区域,石棺葬、铜器、麦等当来自川西高原。
再略向南的滇西,分布着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楚雄万家坝墓地有复合木棺和独木棺,随葬丰富的铜器、陶器、玉石器等,铜器有兵器、工具、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包括5件被认为年代最早的铜鼓。在祥云大波那出土一座木椁墓,椁内的葬具为房屋形铜棺。此两地的墓葬年代有学者认为相当于周代,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西汉。保山昌宁发现东周至西汉时期的墓葬,其中的坟岭岗墓地为土坑墓,大甸山墓地有土坑墓和土洞墓,两地墓葬皆随葬大量铜器,以及陶器、石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等。坟岭岗的铜装饰品,大甸山的铜盒、钺、弯刀等,都独具特色。这个区域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万家坝、大波那、昌宁的墓葬就各不相同,显然属于不同的族属。从文化交流看,宾川、祥云、弥渡等地仍有石棺葬,出土与盐源盆地相近的铜杖头,显示出与川西高原的联系。但再往西、往南到保山一带,这种关联性明显减弱,出现土洞墓、铜弯刀等当地文化的新特点。
云贵高原以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最发达、面貌最独特,被称为石寨山文化,因其族属可以明确为滇人,故也称滇文化,重要考古发现有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羊甫头墓地等。滇文化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大墓有木质葬具,年代大多为战国至西汉。近年在晋宁的河泊所发现青铜时代的遗址,出土两汉时期的建筑、道路、灰坑、水井、墓葬等,河泊所应是滇文化的一个中心。滇文化的青铜器种类极为丰富,有兵器、工具、生活用具、礼仪类器物、乐器、装饰品、马具。表现场景的青铜器最具特色,以贮贝器为例,盖上的立雕场景有祭祀、战争、播种、纺织、纳贡、骑马等。其中一件表现祭祀或“盟誓”的贮贝器,盖上保存的人物形象多达127个。再如扣饰,表现了乐舞、斗牛、缚牛、狩猎、掳掠、祭祀等生动的人物活动。写实的人物形象还有执伞俑、乐舞俑和人物屋宇模型,杖首、兵器、工具、鼓、贮贝器、盒、桶、案、枕、扣饰等普遍雕刻有马、牛、鹿、虎等动物形象。
在云南高原,滇池地区是面积最大的一个盆地,地势平坦,生态环境较好,利于古代人群的定居和文化的发展。滇池地区是西南又一个文化交流带和人群迁徙路线的交汇点,北方地区的文化经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汇聚到滇池地区,长江中游的文化元素也从东向西流传到这里。这些因素使得滇池地区的文化兴盛,地域特色鲜明。从考古发现看,滇池地区在战国至汉代以农业为主,社会等级分化显著,形成了一个明显不同于三星堆神权国家的另一类早期国家。滇池地区因而成为西南青铜时代的又一个区域文明中心。
滇东的青铜文化应为滇文化的一个类型。但曲靖八塔台和横大路墓地存在一种不同于滇池地区的特别葬俗,即墓葬层层叠压,最后形成一个高大的土堆,一座土堆内的墓葬可达数百座。在曲靖师宗大园子发掘出400余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的墓葬,墓地亦为大型土堆状,随葬铜器具有地方特色,存在“毁器”习俗,推测与漏卧有关。在陆良薛官堡有战国至东汉初的土坑墓,葬俗与八塔台等不同,推测墓主人为“靡莫”的一支。
滇南也有青铜时代遗存。元江打篙陡东周时期的土坑墓出土铜器、陶器和玉石器,铜器以兵器为主,包括刃部不对称的钺,也有扣饰和杖首。个旧石榴坝战国时期的土坑墓出土铜兵器、工具,以及陶器、玉石器。个旧黑蚂井两汉时期的土坑墓多有木质葬具,随葬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玻璃器等,铜容器与岭南汉墓中的同类器相近,显现出滇南与岭南青铜文化的联系。
黔西北最重要的遗存是赫章可乐的300多座战国至西汉的墓葬,有汉式墓和土著墓两大类,出土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漆器、木器、纺织品等。汉式墓主要是土坑墓,也有少数砖室墓,有的墓有墓道和棺椁,随葬铜镜、铜钱、带钩、印章、铁器等汉式器物。土著墓最奇特的葬俗是“套头葬”,即用铜釜、鼓等套于死者头部,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茎首为镂孔牌形的铜剑或铜柄铁剑。从墓地墓葬数量多,延续时间长可推测,可乐应是西南古代族群的一个重要定居点。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可乐墓地可能为夜郎的遗存。土著墓中有铜鍪和柳叶形剑等巴蜀式器物,这应是受到了相邻的巴蜀文化的影响;墓中的铜鼓又显示出当地文化与云南青铜文化的交流。可乐出现典型的汉墓和汉式器物,则表明这里是云贵高原接受中原文化的前沿。在黔西南的普安铜鼓山,发现铜兵器、工具和石范,推测该地有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铸铜遗址。
总之,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复杂多样,但也具有共性。一是年代普遍较晚,除滇西北外,其他区域的青铜文化年代大多为东周至两汉。二是遗存以墓葬最多,且类别多样,有土坑墓、土洞墓、大石墓、石棺墓、木椁墓、铜棺墓等,还有叠葬、套头葬。随葬品类别和数量丰富,大都以青铜器为主。目前除晋宁河泊所外,很少发现城邑、中心聚落、大型建筑。滇池地区可能出现了早期国家,其他地区呈现出族群分散、社会结构简单的状态。三是各地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这些青铜器是贵重物,其种类、数量体现出墓葬的等级,但并未形成规范的器用制度,也少见礼器类的青铜容器。显然青铜器并未被赋予过多的观念性内容。除实用器具外,青铜还被用来制作成人物、动物形象,表现人物活动场景,甚至制作成铜棺或套头葬具。青铜器的写实风格非常突出,立雕的人物、动物形象,以及铜器上的动物纹、几何纹等,都生动地表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和身边的事物。云贵高原青铜文化的上述特点,与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青铜文化各有相似之处。
三、西南青铜文化多样性的生成
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与其他区域相比具有鲜明特点,其内部又具有多样性,这些鲜明特点和多样性的生成具有多重原因。
第一,西南是中国地理和生态环境最复杂的区域,地域广阔,地貌多样,分布着平原、盆地、丘陵、高原、山地。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又以山川分隔出无数小区域,各区域相对独立甚至封闭,地貌、气候等存在巨大差异,这从根本上导致了西南地区文化的多样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各区域就产生了复杂多样的文化,如四川盆地的桂圆桥文化、边堆山文化、宝墩文化等,川西高原的营盘山文化、石棺葬文化,云贵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更是类型众多,这些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后续各区域青铜文化的基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延续到青铜时代及之后。
第二,西南地区有着我国最为多样的族群,这与复杂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四川盆地三星堆—金沙文化的族群还不能完全明确,东周时期的部族主要是巴和蜀,蒙文通考证巴蜀区域内还有百多个小诸侯。分布在巴蜀之南、之西的,是众多的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駹最大。其俗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青铜时代的文化,就属于西南夷。
在西南地区丰富的考古材料中,还难以全部确定或对应文献记载的部族,但却明显可见当时多样的族群。冯汉骥由晋宁石寨山青铜贮贝器上的人物雕像和图像探讨族属,根据人物的发式、服饰和活动场景,确定滇族的形象,又从纳贡图景中辨析出滇以外的7组族属不同的人物,从纺织场景中分辨出7组装束相异的妇女。其中的大部分男女大致可以归为“编发”类和“椎髻”类民族。
西南夷中有农耕民族,有游牧民族,有半农半牧的民族,各族的生业、习俗、信仰、社会发展水平相异,从物质遗存上体现出的考古学文化自然不尽相同。
第三,多条族群迁徙通道和文化交流传播带经过西南。一是南北向的交流带。最重要的即前述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它其实也连通我国西北地区,并可以一直通往东南亚。在川西高原和云南高原之间,在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峡谷区,可能存在多条交通路线。二是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都存在的东西向交流通道。其中一条路线是从长江中下游沿长江到成都平原,并一直延伸至川西高原。通过这一路径,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化都深受东方影响,并经此与中原文化相联系。在川西高原的茂县牟托石棺墓中,就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和成都平原的青铜器。云贵高原和南方地区也存在联系,南方的濮系民族在青铜时代可能就已进入云贵高原。战国时,“滇王”可能就来自楚。按《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故秦灭诸侯后,唯有滇王作为楚的苗裔得以留存。童恩正认为,以石寨山古墓为代表的滇文化,就有很多楚的文化元素,比如铜盉、鍪、烹炉、熏炉、镜等基本可视为输入的楚器;铜器纹饰中祀典的陈设、妇女用的肩舆、馘首祭枭、竞渡,以及弩、椎髻、制造铜器的失蜡法等,可能都源于楚。根据《史记》等记载,今珠江水系的南盘江、北盘江等,也是沟通西南与华南的通道。前述个旧黑蚂井墓地,其中的葬俗、铜器、陶器、珠饰,都与岭南汉墓存在共性,墓主或许是来自岭南的移民及其后裔,可能的交通路线包括珠江干流、右江水道和红河水道。
在西南,不同的族群迁徙流动,各种技术、习俗、观念广泛传播,并在各区域土著化,这使得这个区域的文化面貌复杂多变。
第四,铜的材质和青铜器制作技术,造就了西南地区多样的青铜文化,青铜器也成为最能体现西南青铜文化丰富性的物质遗存。青铜器制作技术传入西南后,青铜不仅用来制作实用器具,还用于制作宗教用具和艺术品。由于广泛、活跃的文化交流,制造青铜器的范铸、焊接、锻打、失蜡法等成型技术,镶嵌、线刻、彩绘等装饰技术在西南都有运用,多样的技术使得西南青铜器丰富多彩,并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在中国古代,不同文化的青铜器内涵、风格都不相同。三星堆—金沙文化的青铜器用于太阳崇拜和沟通天地神人,各种神坛、神树、人像、面具、奇异动物等呈现出神秘的美。云贵高原的部分立雕青铜器铭刻了战争、进贡、祭祀、结盟等重要活动,无异于部族的纪念碑。更多的青铜器记录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表现了人们周围的环境与事物,呈现出自然的美。
西南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从考古材料看,大约在商周时期,成都平原形成了以三星堆—金沙为中心的早期神权国家。在滇池地区,大约在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国家形态的社会。
四、西南青铜文化的一体化
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形成的多元文化在青铜时代发展到高峰,在共同构成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文化单元后,逐渐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西南各地的青铜时代的开端不同,各区域文化的一体化的进程和路径也不一致。
四川盆地的一体化进程最早。三星堆—金沙文化大约在春秋早期结束,东周时期四川盆地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变化,巴文化和蜀文化已基本融为一体,受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巴蜀文化。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开始融入中原文化。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多从战国时期开始受到中原文化越来越深的影响,大多数地区的一体化在两汉时期逐渐完成。罗二虎认为,西南夷地区文化的变化大概从西汉中期武帝时期开始,进程相当迅速;文化变迁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以昆明盆地为中心的滇文化,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后迅速变化并最终融入汉文化;第二种是因土著居民的迁移等原因而消失,如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文化;第三种是在接受汉文化影响后仍保持了当地文化的特点,如青衣江上游的东汉墓群表现出的汉文化的影响和土著文化风格的保留。与四川盆地有所不同,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两个区域接受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体化与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的治理有着更直接的关系。
从考古材料看,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体化总体上表现为当地文化元素逐渐减少、消退,中原文化元素不断增多并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一些土著文化元素得以保留的区域也是如此。中原文化对西南地区的强烈影响,最终在整体上导致文化多样性减弱甚至消失,文化面貌呈现出一致性。比如包括船棺葬在内的土著墓葬逐渐消失,石棺葬分布区出现汉式的土坑墓、砖室墓和崖墓,土著的器物被汉式器物代替,带汉字的器物、钱币、建筑材料等大量出现。这种现象在每一个小区域,在绝大多数遗址、墓地都明显可见。如何透过这些显而易见的现象或结果去解释一体化的动因和过程?进一步而言,在生成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多样性的环境、族群、交流等诸种因素并未改变的情况下,文化又因何从多元走向一体?这个问题对于我们认识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历史走向进而理解整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都至关重要。
在解释中国“满天星斗”的格局如何汇聚成内含天下结构且没有中断的中国历史时,赵汀阳认为各区域文明发展程度相近而在技术上各有所长,它们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生存资源,同时,“各地文明之间存在着恰当距离的满天星斗格局使得知识和文化学习交流的诱惑大于战争的冲动,这有可能是中国文明得以形成和平主义基因的一个客观条件”;进而他又根据博弈论构想出“旋涡模型”来解释“满天星斗”之后中国的生长方式,“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资源的博弈活动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自身强化的力量”。“旋涡模型”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上“逐鹿中原”的结果不是以胜者的文化替代败者的文化,而是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同时汇入其他族群的文化,从而形成一个多族群共同参与建构、互用互化乃至重组的新文化。然而西南地区距中原甚远,西南并没有主动进入这个“旋涡”,但最终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仍然融入秦汉文化,原因何在?抛开泛泛而论的中原文化的影响,我们还能找到哪些促进文化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第一,我们要把西南青铜文化的发展走向放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与整体格局中来认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严文明认为这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中国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具有多样性、发展不平衡性,又相互联系,最终中原文化区发展水平较高并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中国史前文化因此形成一个向心结构,如同重瓣的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文化区是花瓣,再外围的其他文化区是第二重花瓣。史前文化的这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基础,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源。如果我们再考察后续的历史,那就可以看到这一重瓣花朵不是静态的,而恰似在不断开放。在新石器时代之后,经过夏商周三代,中原文化区的范围扩大,文化发展水平进一步领先。到秦汉时期,史前时期的第一重花瓣基本上已与花心融为统一的文化区,在此之外的边疆地区构成了新的一重花瓣。正是如此,向心结构成为一种恒久的模式。
在西南地区,从东周时期开始,四川盆地的文化已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至秦汉时,巴蜀地区已不再是边地,原巴蜀疆域以西、以南地区的民族才被称为“西南夷”。考古材料表明,从东周开始,巴蜀地区的文化已明显影响到了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比如茂县牟托石棺墓的青铜器来自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云南昭通水富的土坑墓可能是蜀人南迁的遗存,赫章可乐墓葬中出土了巴蜀式器物。秦汉时期,四川地区的中原文化和人群更多地进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四川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向外传播的新的前沿。秦汉时期四川地区的对外影响不再是西南内部的区域交流,而是成为中原对边疆的向心引力。这应是西南地区青铜文化走向一体化的根源。
第二,秦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开发、管辖和治理。中原王朝对西南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实行郡县制。《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灭巴蜀后即先后设置巴郡、蜀郡、汉中郡、黔中郡。学者研究认为,秦时曾设有蜀侯、筰侯、僰侯等,汉时有滇王、哀牢王、夜郎王、句町王、归义賨义侯、漏卧侯等,等级各不相同。当这些地区融入中原文化程度较高时,便改行郡县制。《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1枚“滇王之印”的蛇钮金印,由此可确认6号墓的主人就是滇王。在曲靖八塔台二号堆69号墓出土“辅汉王印”龟钮铜印。在四川芦山、云南昭通等地,出土当地民族受册封的印章。郡县制和册封制等行政措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理,促使西南地区的土著文化融入汉文化。
同为开发治理措施的是大量移民。从秦灭巴蜀到东汉末年,西南地区出现了三次移民高潮:一是秦灭巴蜀至秦末从秦地和中原向巴蜀地区移民;二是西汉中期开始的巴蜀地区和中原向西南夷地区移民;三是东汉末年大批移民从中原进入西南地区。在四川的青川、荥经都发现有秦人墓,在赫章可乐有与土著墓明显区别的汉式墓。大规模的移民加速了西南地区文化的一体化进程。
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发展交通。西南与其他区域的联系通道早已存在,秦汉时期,除了沿江通行的水道外,又开通了更便于交通的官道。主要包括巴蜀地区联系北方关中地区和西南夷地区的通道,以及西南夷地区内部的通道。现在可知的包括秦代开通的褒斜道、石牛道、阴平道、五尺道,汉代开通的南夷道、西夷道等。官道的开通以及相关设施、制度的建立,加强了地区间的联系。
第三,冶铁技术传入西南,从多方面促进了文化面貌和社会的统一。目前所见西南最早的铁器,应是川西高原牟托石棺墓中的铜柄铁剑,年代可能为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此后川西高原由北向南,开始出现铁制的兵器、工具、容器等。四川盆地战国秦汉时期的铁器主要有兵器、工具、农具和日用器。云贵高原的铁器可能在战国晚期出现,至西汉时骤然增加,有大量兵器、工具、农具、容器,明显存在全铁制品代替铜铁合制器、中原式铁器代替当地器形的过程。
冶铜和冶铁都是一个时代先进的冶金技术,但由于金属性能和制作技术等方面的差异,两者不仅留下了不一样的物质遗存,更为西南地区文化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青铜器造就了西南地区丰富多彩的文化,冶铁技术的普及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何以如此?首先,铁器不同于青铜器,它从开始出现就是实用的兵器和工具。从世界范围看也是如此,青铜器广泛作为艺术品,而铁器更多的是实用器,实用铁器本身就不再具有多样性。其次,冶铁术作为一种来源更具单一性的先进技术传播到各地,所生产的铁器和相伴随的文化元素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在西南地区,实用铁器逐渐成为中原式器物。汉武帝时期,中央为加强对全国经济的控制和集权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其中就包括“盐铁官营”,将冶铁收归政府管理,不产铁的郡设铁官管理铁器专卖等。这类官营政策,又加深了技术、产品的统一。
再进一步看,冶铁业从多方面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统一。铁器广泛用于农业、手工业、水利、道路工程、军事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能力,开通了区域间的交通路线,加强了各地的往来,对经济、社会、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铁器的出现与普及,使中央王朝得以有效开发和治理包括西南在内的边疆地区。
第四,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文化、社会的统一性。不同类型的生业是西南地区青铜文化多样性的原因之一,在中央王朝加强对西南的开发以及铁器普及后,西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得以发展,形成了文化一体化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发展。在四川地区,农业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时期已有稻作农业,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在青铜时代的西南夷地区,也有农耕民族。
在西南,铁器于战国秦汉时期开始用于农业。成都平原战国时期的铁器较少,秦汉时期的铁器增多,其中就有镰、锸、犁等农具。在川西高原,茂汶、理县、雅江、宝兴等地的石棺墓出土了铁锸、锄、镰、铚。秦汉时期铁农具对西南地区的农业发挥的作用还难以估量,但应有一定影响。
从铁农具以外的其他考古材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到农业在西南地区的概况和重要性。在西南的汉式墓中常见一类特别的随葬品,即陶质或石质的水田与陂池模型,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稻田的设施。另一类重要遗物是汉墓中的画像砖,描绘有农业生产的场面,包括播种、薅秧、收割、谷物加工等,由此可了解水稻耕作的主要程序。晋宁石寨山贮贝器的人物形象,表现有“祈年”“播种”“报祭”“上仓”场景,反映了祈年与秋收等与农事相关的典礼;还有青铜人物屋宇模型,表现的是与土地“孕育”相关的信仰。
第五,汉字成为统一文化和社会的最为关键和持久的因素。中国成熟的文字系统出现在商代晚期的殷墟,同一时期其他区域没有产生文字。殷墟的文字由少数统治者和社会精英掌握,成为统治社会的重要工具,这使得文字主要见于商文化的分布区,在其他区域,只有从中原流传出去的商式铜器上才有铭文。西南地区直至战国时期才出现文字。四川荥经、蒲江、青川等地出土的战国铜矛和戈上有“成都”铭文,漆器上有汉字“成”“成亭”,涪陵小田溪出土的铜矛上还有“廿六年蜀守武造”。在云贵高原,除“滇王之印”等汉字印外,大量的文字材料出自晋宁的河泊所,那里新出土两汉时期的带字简牍2000余件、封泥800余枚,还有带字瓦当。封泥有“益州太守章”等各级官印与私印,简牍内容涉及政区建置、职官制度、赋税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在贵州安顺宁谷的汉代大型建筑遗址也出土了“长乐未央”瓦当和隶书木牍。
汉字对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它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凝聚力,使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汉字及其书写的思想系统对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同样重要。人们在使用一种文字的同时,自然也就接受了文字承载的知识体系与观念体系。汉字因其不同于其他文字的重要特性,对于形成文明统一性的作用更为显著。赵汀阳指出,汉字作为象形文字能够独立于语音存在且易被理解,因而天然地具有普遍的可分享性,所有族群都能使用,有利于消除种族隔阂和语言限制;而用汉字构筑的精神世界或知识生产系统也成为中原最具有特殊性而无可替代的优势资源。王树人认为,汉字凝结和传递了汉民族从牧猎时代到农耕时代社会发展的信息,以及与上述社会生产相应的氏族家长制、尊天为神等伦理、政治、思想的信息,具有深刻的历史性;同时还认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形象中心主义源于汉字的象形性根基。如此,人们接受汉字,积淀在汉字中的历史就成为共同的历史,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受到共同的影响。
早期的汉字还强化了书写载体的神圣性与权威性,这一点不仅印证了文字的力量,而且也说明了文字是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有效手段。商代刻写在甲骨上的文字用于占卜,铸于青铜器上的文字则与青铜礼器成为一个整体,深化了文字记述的内容和礼器的含义。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汉字,令人瞩目地集中出现在王印、官印、封泥或者高等级建筑的瓦当上,这些器物不再是礼器,但却是权力的象征物。汉字同时出现在西南地区出土的汉代货币上,在盐源还发现了王莽时期带“永遵”等汉字的衡器。秦统一了六国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统一后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器传入西南,促进、巩固了西南文化和社会的一体化进程。
在西南地区,多线索的区域沟通生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并塑造了当地文化包容的品格,文化的包容性又使随后的文化融合得以实现。秦汉王朝建立后,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增强,中央王朝推行的包括郡县制在内的多种管辖和治理方式、冶铁技术、农业、汉字,在历史根源和文化包容性之外,又分别从制度、技术、经济、思想等方面促进了一体化。这些关键的要素,突破了地理环境与族群的界限,使西南地区多元的青铜文化最终融入统一的中原文化中。
〔本文注释内容略〕
原文责任编辑:郭飞 责任编审:晁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