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作为一个名词首先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法国,即法语civilisation。这一概念是在法国启蒙运动和对外殖民扩张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作为一种观念,反映了当时法国人以非欧洲民族的“野蛮”为参照所具有的一种对自身社会“进步”的优越感。因此,在近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中,始终隐含着一个非西方的“野蛮”他者,二者构成了西方“文明”观念中的基本要素。从词源来看,西方“文明”一词的词根与拉丁语civilis(市民的、公民的)、civis(市民、公民)有关。可见,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与古代罗马的“市民”(公民)观念有着语意上的渊源关系。此外,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作为一种体现自我优越性的意识形态,其“文明”特性通过对比描述“他者”的“野蛮”而建构起来。从词汇和概念的演变来看,英语中的barbarous(野蛮)来自拉丁语barbaros,而barbaros又来自古希腊语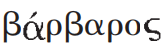 。因此,现代西方“文明”概念在作为名词出现之前有其深远的观念文化传统,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因此,现代西方“文明”概念在作为名词出现之前有其深远的观念文化传统,与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有着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古希腊人的
“蛮族”观念与文化优越感
古希腊虽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希腊人却形成了统一的民族意识,他们自称“希腊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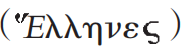 ,将外族称为“蛮族”
,将外族称为“蛮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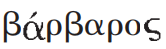 。希腊人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与邻近民族的差异,称这些民族为发出“巴巴”音的说话者,于是
。希腊人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与邻近民族的差异,称这些民族为发出“巴巴”音的说话者,于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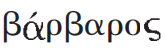 就用来指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发出“巴巴”音的外族人。虽然此时的“蛮族”还没有现代词汇贬称“野蛮人”之意,但它的使用,已初步具备了近现代欧洲人用来指称非欧洲人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价值评判。基托说:“要是我们问一个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不同于蛮族……他可能会说,而且事实上的确也这样说了:‘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
就用来指那些不说希腊语而发出“巴巴”音的外族人。虽然此时的“蛮族”还没有现代词汇贬称“野蛮人”之意,但它的使用,已初步具备了近现代欧洲人用来指称非欧洲人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因为它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政治价值评判。基托说:“要是我们问一个希腊人,到底是什么让他不同于蛮族……他可能会说,而且事实上的确也这样说了:‘蛮族是奴隶,而希腊人是自由人。’”
把蛮族看作“奴隶”,也就意味着他们不享有希腊人的“自由”,没有希腊城邦中“公民”所具有的权利和生活方式。这种蛮族受到“奴役”而希腊人享有“自由”的观念,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的希波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且通过这次战争得到强化。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写了大量希腊人为捍卫“自由”而抵抗波斯人的故事。当然,古希腊人所说的“自由”并非现代语义的“自由”,但无论怎样,在希腊人的价值判断中,它无疑是东方“蛮族”缺乏的东西,能够体现其文化优越性。
希腊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使希腊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对东方民族的野蛮化认知达到一个高潮。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便是很好的例证,通过对波斯人战败的描写,从希腊人的视角想象和建构起一种波斯人的“他者”形象。戏剧中这种形象建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指出的,波斯人通过希腊人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希腊人的想象而得到表述。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全部人类所居住的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希腊,认为希腊位置适中而造就了优秀的希腊人,一旦希腊各族统一起来,便可统治全世界。
古代希腊人认为其城邦及城邦生活完全不同于周边“蛮族”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东方的波斯人没有“自由”,北方的“蛮族”过着游牧的、非城市的、没有教养的生活,而希腊人则生活在城邦之中,有文化和有教养,享有“自由”并过着公共政治生活。因此,古代希腊人在“蛮族”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优越感,与希腊人的城邦生活和城邦观念密不可分。大约在公元前5—前4世纪,雅典贵族中产生了一种“优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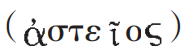 观念,这个词有“在城市中培养起来”的意思,因此这种观念正是通过与乡村生活的对比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约翰·海明威认为,古希腊人的“优雅”观念接近于后来英语中civility所表达的含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文雅(civility)标志着希腊人胜过非希腊世界的优越性”。
观念,这个词有“在城市中培养起来”的意思,因此这种观念正是通过与乡村生活的对比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约翰·海明威认为,古希腊人的“优雅”观念接近于后来英语中civility所表达的含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文雅(civility)标志着希腊人胜过非希腊世界的优越性”。
古罗马人眼中的
“优雅”与“野蛮”
古代罗马人的公民观念及其自我意识中,也存在着希腊人那样的文化优越感。拉丁语urbanus包含“有城里人风范的、优雅的、有教养的”等意思,urbanitas用来描绘城里人即罗马市民(公民)的一种品质——优雅、有教养,与之相对的词是rusticitas(乡巴佬行为、粗野)。在古罗马作家的作品中,urbanitas这种罗马人所固有的品质,是外国人和罗马的外来民族所没有的,也是乡下人不具备的。
西塞罗在《论义务》中提出,政治家应具有智慧、正义、刚毅、节制的美德,而美德可以从整体与个体两个不同的层次进行阐释。人类拥有整体上区别于动物的优越性,而在个体中,一部分人又有他人不具备的美德,这正是西塞罗所要表达的罗马人优越于“蛮族”的地方。西塞罗认为,政治家的美德通过心灵的培养而实现。因此他在《图斯库兰讨论集》中谈到哲学的作用时,以“耕作土地”(cultus agrorum)比喻“心灵的耕耘”(cultura animi),提出“哲学是对心灵的教化”。从此,cultura一词便具有了“文化”的含义。西塞罗通过这一比喻,使cultura一词由原本的“耕耘、栽培”引申出“教化”的含义,成为第一个使用“文化”一词的人。cultura一词作为“文化”意涵的用法在17—18世纪的西欧著作中重新出现。到19世纪,它在德国学者的倡导下成为一个与“文明”同等重要的概念,并造成了这两个概念的混用。
在罗马世界,除了“优雅”的公民之外,还有“野蛮人”。罗马人关于“野蛮人”的概念是从希腊人那里借鉴来的。在罗马人看来,衡量是否“野蛮人”的标准,除了语言的不同外,还包括行为举止和品性的差异,亦即“野蛮人”是一个文化概念。西塞罗在《国家篇》中描写了西庇阿与莱利乌斯之间的一段对话。莱利乌斯说,按希腊人的说法,所有的人要么是希腊人,要么是野蛮人,这样的话,罗马人恐怕是野蛮人。但接着他补充道:“如果[野蛮人]这个名词是根据人们的举止而不是其语言来适用的话,那么我并不认为希腊人比罗马人更少些野蛮。”西庇阿接着说,如果只考虑品性,不考虑种族,那么“通情达理”的罗马人就不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这表明,罗马人在借鉴希腊人的“野蛮人”概念时,不只是从语言来判断,人的举止和品性也是重要衡量标准。那些居住在罗马辖地之外举止粗俗、不通情达理的人才是“野蛮人”。这说明罗马人在区别“自我”与“他者”时,更注重文化因素和文化认同,这种重文化而轻种族的倾向,与212年罗马皇帝将公民权授予罗马帝国境内全体自由民的举措相一致。正因如此,罗马人在表达自己优越于周边其他种族的观念时,从自然环境造成的身体和精神差异来理解罗马人不同于蛮族。例如,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对罗马民族的优越性作了解释,认为“神意把罗马市民的国土布置在极好的并经过调和的地区,以便能够获得统治大地的权力”。
由上可见,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以“有教养的自我”和“野蛮的他者”建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在近现代西方学者视希腊罗马文化为西方文化之源的情况下,近现代西方“文明”观念与这种“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文化的和民族心理的联系。而且,希腊人和罗马人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其一种以自身社会为坐标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的内涵,在许多方面与近现代西方“文明”概念中的基本要素相吻合,并通过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西方“文明”话语体现出来。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